第一章 范稳的藏地书写
第一节 汉藏差异下的作家身份
当代文学的藏地书写体现出西藏文化的精神:神秘感,浪漫风格以及作为西藏文化精神之根的淳朴的民族魂。在西藏和平解放 67 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当代文学的藏地书写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以饶介巴桑的诗歌和徐怀中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为代表,主要是写藏地之美、淳朴的民风以及汉藏友谊;60 年代,以电影《农奴》为代表,主要歌颂解放军;80 年代,以扎西达娃等人为代表,主要是写藏地的神秘;90 年代,以马丽华的散文和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为代表,全面描绘西藏历史和文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杨志军的《藏獒》等为代表,主要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
藏地书写是不同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藏地,它是由多民族作家共同构建的精神家园。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大批的藏地作家,以游记、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从自然风物、人文历史以及文化变迁等角度对藏地进行书写,同样的一个西藏,同样的一片大地,多数的作家都将西藏描绘成雄浑苍茫、博大粗粝的原始“荒原”,但不同民族的作家在对它的书写上却是不径相同的。这其中包括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等藏族作家,马丽华、毕淑敏、李佳俊等汉族作家,而范稳带着强烈宗教情结的藏地书写在众多藏地作品中旗帜鲜明的存在着。
以扎西达娃、阿来为代表的本土藏族作家,作为在西藏地区成长生活的人,是古老藏地的讲述者,也是新西藏变革的亲历者。同范稳等汉族作家不同,他们自幼生活在藏地,接受着传统的藏族教育,有厚重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背景,同时也承载了藏族文化历史的伤痕,经历着西藏发展的冲击。他们在新时期藏地内外文化的交流下形成了对民族身份与文化的强烈认同与归属感,这里是他们的生命之根与创作源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了强烈的家园意识。降边嘉措等早期藏族作家着力寻求外界的文化认同,对自我的民族文化进行“突围式”的文学尝试。而在后期藏族作家的创作中,在文化认同上表现更为突出,他们主要从民族文化方面来对藏地进行构建,将藏地描述成为一个理想的家园,以完成对自我民族文化的守望。作为藏地生活的参与者,藏族作家比汉族作家更深刻的感受着藏地的厚重历史,同时也体会着藏地难以磨灭的沉重伤痕。所以,无论是早期藏族作家的作品中,还是扎西达娃、阿来等后期藏族作家的创作中,藏地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家园。但这更体现了他们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与热爱,进入新时期以后,藏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有了全新的思考,而藏族作家索朗更是提出,藏族作家要坚持用藏文进行文学创作。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和高度的自我文化认同是藏族作家与范稳等汉族藏地作家区别最大的创作特点。
...........................
第二节 范稳作品中构建的藏地环境
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对解放初期的藏地社会作了如此的评价:“种种证据表明,1950 年以前的西藏既不是神秘的‘世外桃源’也不是‘人间地狱、西藏人的生活很艰苦??西藏是一个不知怎样幸存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世纪社会。”而范稳的“藏地三部曲”中故事的发生时间是 20 世纪的一百年间,正是西藏从“中世纪社会”的旧西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西藏的特殊时期,是西藏地区长久以来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甚至就连《水乳大地》的章节直接以年代命名。
一、“藏地三部曲”的历史背景
范稳同其他汉族藏地作家一样,对藏地的书写来自于他十年间多次以茶马古道为依托从云南进入西藏的游历与调研,“藏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地就设定在藏东地区的滇藏结合处,地处卡瓦格博峰脚下澜沧江峡谷里。峡谷两岸不同家族世代的恩怨情仇、雄奇的自然景观、恶劣的生存环境、各民族间的资源掠夺、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的角力搏杀使故事得以顺利展开。
在“藏地三部曲”中,范稳着力展现了在这片遥远原始的大地上,人与大地的共生共融,展现了藏民对自然的原始崇拜,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原始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人们崇敬自然敬畏神灵的信仰基础,虽然范稳在作品中并未刻意渲染当时藏民生存环境的恶劣,但当时藏地落后的社会形态却是三部曲故事的基础背景。
..........................
第二章 范稳笔下的藏地宗教
第一节 西方宗教带来的冲突与共融
范稳从云南出发,沿着滇藏公路一路向西,入藏的第一站就是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的盐井乡,这是藏区与范稳作品中故事发生地对应的现实区域,位于横断山脉澜沧江东岸,东北与四川接壤,南部比邻云南德钦,向西便能直入藏区腹地,自古是连通滇藏的重要通道,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当然,这也是西藏仅有的天主教堂所在地,是天主教与其教众在藏地唯一的生存之地。正如《大地雅歌》结尾描述的教堂村一样,纳西族的东巴教、新传入的天主教以及传统的藏传佛教在这个峡谷里共存着。盐井天主教堂建于 1855 年,它是整个藏区仅存并仍在使用的天主教教堂,见证了西方宗教传入藏地的血泪史,也证明了藏地的神奇——能接纳和包容不同的宗教与信仰。
第二节 范稳作品中构建的藏地环境
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对解放初期的藏地社会作了如此的评价:“种种证据表明,1950 年以前的西藏既不是神秘的‘世外桃源’也不是‘人间地狱、西藏人的生活很艰苦??西藏是一个不知怎样幸存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世纪社会。”而范稳的“藏地三部曲”中故事的发生时间是 20 世纪的一百年间,正是西藏从“中世纪社会”的旧西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西藏的特殊时期,是西藏地区长久以来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甚至就连《水乳大地》的章节直接以年代命名。
一、“藏地三部曲”的历史背景
范稳同其他汉族藏地作家一样,对藏地的书写来自于他十年间多次以茶马古道为依托从云南进入西藏的游历与调研,“藏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地就设定在藏东地区的滇藏结合处,地处卡瓦格博峰脚下澜沧江峡谷里。峡谷两岸不同家族世代的恩怨情仇、雄奇的自然景观、恶劣的生存环境、各民族间的资源掠夺、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的角力搏杀使故事得以顺利展开。
在“藏地三部曲”中,范稳着力展现了在这片遥远原始的大地上,人与大地的共生共融,展现了藏民对自然的原始崇拜,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原始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人们崇敬自然敬畏神灵的信仰基础,虽然范稳在作品中并未刻意渲染当时藏民生存环境的恶劣,但当时藏地落后的社会形态却是三部曲故事的基础背景。
..........................
第二章 范稳笔下的藏地宗教
第一节 西方宗教带来的冲突与共融
范稳从云南出发,沿着滇藏公路一路向西,入藏的第一站就是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的盐井乡,这是藏区与范稳作品中故事发生地对应的现实区域,位于横断山脉澜沧江东岸,东北与四川接壤,南部比邻云南德钦,向西便能直入藏区腹地,自古是连通滇藏的重要通道,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当然,这也是西藏仅有的天主教堂所在地,是天主教与其教众在藏地唯一的生存之地。正如《大地雅歌》结尾描述的教堂村一样,纳西族的东巴教、新传入的天主教以及传统的藏传佛教在这个峡谷里共存着。盐井天主教堂建于 1855 年,它是整个藏区仅存并仍在使用的天主教教堂,见证了西方宗教传入藏地的血泪史,也证明了藏地的神奇——能接纳和包容不同的宗教与信仰。
范稳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三部作品中有两部都书写了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范稳在《水乳大地》开篇描述一个新宗教强烈又充满了“阴谋”的侵入:西方的传教士凭借着军事力量所支撑的政治强势、经济优势和先进的医学敲开了西藏宗教沉重的大门,甚至由落后迂腐的政府为他们提供了武力支援。然而先进的文明与自视甚高的宗教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更高尚,甚至已经丧失看似落后民族的质朴与谦逊。恩格斯在论述文明的进步时说:“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28作品中顿珠活佛更是发出这样的扣问:“如果一个国家和他的民族,连慈悲都没有,又何谈文明呢?”
.............................
第二节 “藏地三部曲”中的小众宗教
范稳曾经在三部曲的首部扉页上引用了马克斯·缪勒的话:“谁如果只知道一种宗教,他对宗教就一无所知。”在作品中,范稳不只是书写西藏独有的宗教,而是借由多种宗教在藏地的发展与兴衰展现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恩怨纷争。除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故事里还有少部分篇幅讲述了藏地的本土宗教本教和纳西族的东巴教。
一、本教法师的失落
在佛教传入西藏前,藏民信仰的是起源于原始宗教本土宗教——本教。范稳笔下的本教,是原始本教,并不能与目前仍有传承的雍仲苯教混为一谈。原始本教是由植根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一种巫教发展而来,“从属性和内容上看,兼有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二重性。”原始宗教多是多神崇拜,崇拜天地、山川等一切自然物。本教的原始宗教性质在学术上被泛称为“灵气萨满教”。而人为宗教是与原始自然宗教相对的,具有较高级的人为痕迹的宗教,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教义著作等传承。原始本教是佛教传入藏地之前的藏族先民信奉的藏区固有的宗教,是人们在大自然的压力下产生的原始自然崇拜,没有深厚的宗教哲学理论。
在西方传教士运用他们的狡诈为自己的宗教赢得了牛皮大小的土地建盖教堂时,本教的法师已看到了宗教斗争的硝烟已然升起,并发出了他的预警:“火最早是从木头中取出来的,但毁灭森林的就是火”、“人们循声望去,只见本教法师敦根桑布正骑着一面鼓从峡谷上空飞过。”36但这个落寞宗教的法师久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的突然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大家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法师的神奇法力之上:他长久不变的容颜,他降伏魔鬼的法术,以及他与喇嘛斗法失败的故事上。
......................
第二节 “藏地三部曲”中的小众宗教
范稳曾经在三部曲的首部扉页上引用了马克斯·缪勒的话:“谁如果只知道一种宗教,他对宗教就一无所知。”在作品中,范稳不只是书写西藏独有的宗教,而是借由多种宗教在藏地的发展与兴衰展现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恩怨纷争。除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故事里还有少部分篇幅讲述了藏地的本土宗教本教和纳西族的东巴教。
一、本教法师的失落
在佛教传入西藏前,藏民信仰的是起源于原始宗教本土宗教——本教。范稳笔下的本教,是原始本教,并不能与目前仍有传承的雍仲苯教混为一谈。原始本教是由植根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一种巫教发展而来,“从属性和内容上看,兼有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二重性。”原始宗教多是多神崇拜,崇拜天地、山川等一切自然物。本教的原始宗教性质在学术上被泛称为“灵气萨满教”。而人为宗教是与原始自然宗教相对的,具有较高级的人为痕迹的宗教,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教义著作等传承。原始本教是佛教传入藏地之前的藏族先民信奉的藏区固有的宗教,是人们在大自然的压力下产生的原始自然崇拜,没有深厚的宗教哲学理论。
在西方传教士运用他们的狡诈为自己的宗教赢得了牛皮大小的土地建盖教堂时,本教的法师已看到了宗教斗争的硝烟已然升起,并发出了他的预警:“火最早是从木头中取出来的,但毁灭森林的就是火”、“人们循声望去,只见本教法师敦根桑布正骑着一面鼓从峡谷上空飞过。”36但这个落寞宗教的法师久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的突然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大家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法师的神奇法力之上:他长久不变的容颜,他降伏魔鬼的法术,以及他与喇嘛斗法失败的故事上。
......................
第一节 宗教是集体潜意识的选择 ......................... 27
第二节 爱的力量超越一切 .................... 33
第三节 向内寻找灵魂的归处 ..................... 33
第三章 范稳作品中的灵魂寻找
第一节 宗教是集体潜意识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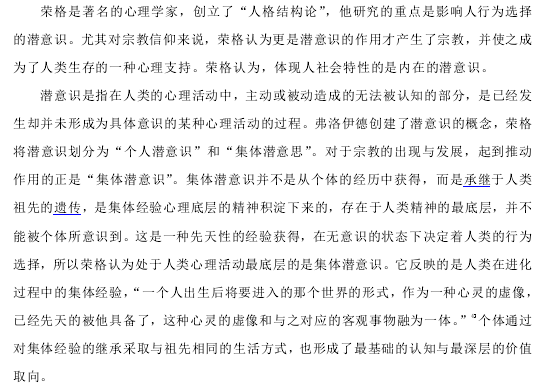
................................
结语
同藏族作家相比,汉族作家进行藏地小说创作时没有先天的文化优势,但范稳用十年时间对藏地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深入的学习了西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这奠定了他创作“藏地三部曲”的深厚基础。同时,范稳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神灵的自发敬畏也渗透到他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中。他作品中带有强烈的宗教情怀为我们呈现出他对神灵的敬畏和对大地的谦卑,这是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将范稳成书于 1999 年的散文集《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看作是“藏地三部曲”的准备之作,十年间范稳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纵观范稳“藏地三部曲”的整个作品,虽都是厚重宏大的讲述,但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水乳大地》中,生硬又跳跃的布局,影响文本的阅读效果,仅仅是讨巧的布局设计;《悲悯大地》中,过多的佛教理论叙述降低了作品的故事性,偶尔出现的田野调查将整个故事的发展与年代打断,极易造成混乱。最终,《大地雅歌》作为三部曲的结尾出现,在成书年代是最晚的,也是三部作品中范稳的写作最成熟的,多层次的作品构架,多角度的故事展开,使文本具有更强的阅读性。但是相较于藏族作家,范稳缺少了对藏地历史的深刻体会,他笔下的藏地生活缺乏深度。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