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孙犁的作品与思想既对时代有超越性的知解,也有不顺应潮流的保守,看似不与时俱进,实则正是孙犁创作个性与艺术追求的体现。
第一章 孙犁晚年的“边缘”心态
第一节 特定时代的隐匿与守持
孙犁晚年的“边缘”状态是历经数次政治运动,尤其是镂心刻骨的“文革”之后自然的“经验”选择。可以说,孙犁晚年的人格蜕变、散文风格的形成起始于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孙犁个人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身边朋友遭到的凌辱,几次“自杀”体验,给本就敏感脆弱的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创痛。孙犁“文革”后的写作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内心戒惧较深,愈加谨慎,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这也为他晚年的“边缘”选择增添了主观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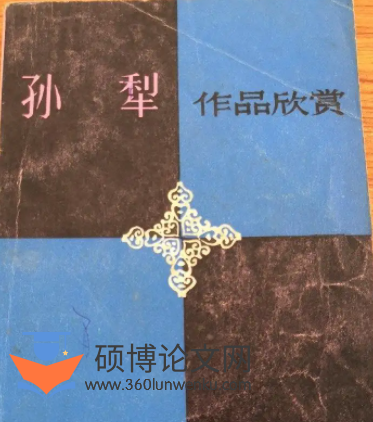
文学论文怎么写
一、身份与心态的双重转换
早在四十年代,孙犁的心态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文革”前的数次运动,是其谨小慎微心态的发展。“在四十年代初期,我见到、听到有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者说话受到批判,搞得很惨。其中有的是我的熟人。从那个时期起,我就警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1]朋友的境遇让孙犁开始紧张起来,而土改运动使他直接感受到了革命对其本人及家庭的冲击。于个人来说,1947年冬季,冀中区土地会议召开,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缺乏政治经验,孙犁还在会议中就因对个人家庭成分问题与众人看法不同而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作品《织席记》被指为“丑化农民”,《一别十年同口镇》因肯定进步富农被认为“有立场”问题,《新安游记》因将街道方位搞反被指为“客里空”,在《冀中导报》被整版批判;在被分配到的饶阳县张岗小区时,孙犁在严冬季节毅然剪掉了长发,穿着草鞋踯躅在张岗大街上,悲壮之余,足见此时孙犁心情的低落。于家庭来讲,父亲辛苦一辈子盖起来的房屋被拆走分给贫农,只剩下三间正房;父亲逝世,连为其立碑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家中无劳动力,一家老小的生活陷入困境,还因孙犁个人的问题加大了家乡土改对家庭的斗争力度。1947年夏随工作团在博野县参加土改试点时,孙犁就对一些极“左”做法如对地主残暴的“一打一拉”灵活政策表示无法理解,并把那些斗争地主的行为视作“恐怖行为”,后来在晚年的《<善闇室纪年>摘抄》和芸斋小说《石榴》中对这些情景有反复的记述。这些事件都打破了孙犁过往的认知,加重了他思想上的苦闷,用孙犁自己的话说在进城初期他“已近于身心交瘁状态”[2]。
.................................
第二节 疾病体验与文风转变
1982年联合国第37届会议规定时序年龄60岁以上即为老年。1976年孙犁写作“文革”后第一篇文章的时候63岁,此时已经进入了他人生的老年期。晚年,或者说是老年时期,是人生历程中相当特殊的时段,老年往往伴随生理功能的衰退与心理结构的改变,对于在创造性领域工作的作家来说,衰老可以视作其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捩。只有关注到作家晚年心理和生理的变化,才能真正进入其晚年创作,洞悉其选择的原因。孙犁的晚年特征主要体现在各类老年病的侵袭、长期困扰他的“神经衰弱”在晚年的持续发展,以及视力、记忆力、对外界适应能力的严重下降等。这些晚年特征表现在生理上:是孙犁的精力和体力都大幅衰弱,无法从事长时间的伏案写作,这也是他由写小说转向写篇幅相对短小的散文的直接原因之一;在心理上,长期的疾病使孙犁本就内倾的心态更加压抑敏感,在晚年作品中氤氲出无尽的苍老感。除此之外,散文、杂文等相对自由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更能体现晚年孙犁真实的感情形态。
疾病是研究孙犁的一把重要的钥匙,有研究者指出:“‘病’已经成为解读孙犁的一个重要的意象或编码。”[2]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孙犁幼年时的“惊风疾”、1956年的“神经衰弱”等病因及病情的阐释都比较完备了,但对孙犁跨入老年期之后各类疾病给他生理、心理及写作带来的影响却关注较少,这也为本文留下了阐释空间。
.........................
第二章 在“边缘”处坚守文学理想
第一节 对真善美的回忆与追寻
作为“文革”受害者之一的孙犁,在“伤痕”“反思”大潮席卷文坛,直指十年“文革”之时,他没有以受难者的身份去检视历史,而是采取理性审视的态度,表现出对历史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在大量文学作品批判“文革”时,孙犁散文的基本笔调却是回忆,高唱过去的歌,信笔直书,真情流放,以赤诚的心再次弹奏起人性美的曲调。孙犁晚年的回忆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写人叙事、怀念故友,而是要在绵长的回忆中表现和传播一个“群体”的思想。这个特殊的“群体”共同经历了过去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阶段,见证着国家的发展,怀揣着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可以说是“为革命而文学”,也是“为文学而革命”[1]。孙犁用朴素的文字再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书写一部知识分子或是革命文艺战士的战争史,是在彰显其个人的生命追求,也是在以“以逝者之所长,补存者之不足”[1]。用昔日的美好观照现实,以寓沉痛于悠闲的笔调体现时代的荒谬。
一、文学主潮中的选择
“情感的缺乏控制的抒发与宣泄。这特别表现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那几年的创作里。”[2]孙犁在文章中多次表达了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种声嘶力竭地控诉方式存在的忧虑和异议。在其风头正盛时,孙犁就认为当前描写十年动乱的小说缺乏深度与观察,对罪恶行径的谴责停留在刻画“游街”“批斗”“牛棚”等表层的东西上,“如果写,今天则须进一步,深挖一下:这场动乱究竟是在什么思想和心理状态下,在什么经济、政治情况下发动起来的?为什么它居然能造成举国若狂的局面?它利用了我们民族、人民群众的哪些弱点?它在每个人的历史、生活、心理状态上的不同反映,又是如何?”[3]作为一位与民族共同成长,饱经历史沧桑的老战士,孙犁的每一个叩问都相当沉重。他渴望看到更深刻、更能凸显实质问题的“文革”反思,而不是大肆地宣泄伤感情绪,把“文革”放在恶人当道的历史背景下,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逃避对现实和历史的责任与担当,忽略探索“文革”发生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以及对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下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孙犁同时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流于表面情绪的书写也作出了理性的解释,认为这一段历史本身在文学上的呈现就有过多的纠缠和困难,还需要时间的积淀才能完成。孙犁对“伤痕文学”等不同角度的思考与宽容的态度展现了其老作家的思想深度和强烈的历史关怀。
..............................
第二节 城乡对视下的道德忧思
孙犁是天津这座城市的“他者”和“边缘人”,在农村成长、工作过的他,与都市有一种天然的隔膜感。故园的梦和乡村美好的人性人情一直萦绕在孙犁思想意识的深处,“梦中屡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1]是晚年蛰居都市一隅的孙犁真实的情感写照,也是他人生进入晚途的重要表征。孙犁不仅在情感上始终依恋乡村,保留着农村质朴的生活习惯,还在文笔间描绘乡村的芸芸众生相,对苦难的农民抱以怜悯和同情,寄托对农村、农民改变命运的美好希冀。对城市生活有诸多不适应的孙犁,在散文中以农村和城市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在物欲膨胀的时代,以生活的城市大院为叙事视角,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文化反思。
一、对乡村的精神牵念
对城市的疏离源于对乡村的依恋,晚年孙犁借助乡土的回返将自我与城市现实生活隔绝。1949年1月就进入天津市区的孙犁,对农村一直葆有深厚的感情。农村不仅是孙犁成长成熟的地方,也是他的精神家园,在晚年孙犁的乡土意识更是有增无减。
晚年散文中,孙犁多次谈到他对乡村的无限情思和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和后来接触的山区农民„„我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在嘈杂骚乱无秩序的环境里,我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2]“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先后在农村生活、工作,近三十年。我很爱我的故乡„„直到现在,我已经很老了,还经常不断地做梦,在它那里流连忘返。”[3]故乡的风俗人情养育了质朴的孙犁,是他的文化资源所在,散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乡村的眷恋与钟情。每天都在思念农村的孙犁连珍视的藏书中也有不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自述购买它们只是因为来自农村,对农书易生感情。孙犁自然地把自己视为农村的一员,将农村看作他心灵的栖息地,与在而不属于的城市生活对立,致使晚年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他一直有一种流落异乡的孤独感。
.................................
第三章 “边缘”背后的文学思想 ..................................... 44
第一节 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复归与深化 ........................... 44
一、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 44
二、“新潮”之外的趣味别择 .................................. 46
结语 ......................... 58
第三章 “边缘”背后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 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复归与深化
孙犁的晚年写作自觉承担起了连接现代与当代文学史的重任,这主要体现在其对“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发展。对孙犁来讲,文学研究会、鲁迅以及左翼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技巧和方法上,更多的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内化于心,是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彰显。晚年孙犁将青年时一直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进行深化和拓展,在现实主义中融入人道主义的内涵,将创作内容的真实和作家思想意态的真诚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在纷繁喧嚣、多种文艺思潮流行的当代文坛,在现代主义崛起,现实主义受到严峻挑战之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延续“五四”开创的文学精神血脉,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进行坚持和开掘,不仅是对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些倾向的纠偏,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别样的思想资源。
一、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青年孙犁以《现实主义文学论》等作品和文艺战士的身份多角度竭力阐释现实主义,树立了为文学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晚年现实主义精神和写作仍然贯穿在这位耄耋老人的琐谈、短评、读书记中。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孙犁就在作协代表大会短暂的发言中强调,要把丢掉的现实主义拾起来,后来又在读书记中恳切地说道,“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1]在文坛尚且纷繁复杂,大多数人还沉浸在伤感中的时候,孙犁率先举起了现实主义这面从“五四”传来的旗帜。

文学论文参考
.............................
结语
孙犁晚年“边缘”的生活状态近似于庄子笔下的“游世”,在精神层次上保持着人格独立,同时又真正置身于现实生活中,但大多数时候选择的却是冷眼观世。在孙犁身上始终是儒大于道的,“边缘”是政治形势、身体原因、个人性格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智慧,看似“边缘”的隐默,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坚守”。新中国成立前后和“文革”时期急剧变化的政治环境,晚年疾病影响下生理功能的衰退和心理结构的改变,加之与世无争、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性格等,诸多原因造成了孙犁“边缘”的生存状态。而孙犁“边缘”的背后有着对文学现状的冷静思考,在大转折的时代,孙犁以自己的文学理想来观照社会、文坛的新变化,从未被文坛风尚所裹挟、诱惑,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表面的伤痛中执著地追求真善美,在缅怀故旧、忆念往昔的同时给予“文革”更深层次的反思;固执地依恋农村人与事的美好,寻求精神还乡,在城市与农村的对照下,对都市异变的人性发出道德忧思;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表达对文学商品化的忧虑:在与古籍的跨时空对话中,寻找贯通古今的哲理和规律。在文学思想上,孙犁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民族性等问题作了一些“不达时宜”的思考。他的发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但时间证明,孙犁的隐忧和这种“边缘性”的思索很有价值,也非常具有灼见。
“边缘”为孙犁在时代洪流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避免了趋时附世,他说:“我想,既然从事此业,就要选择崇高一点的地方站脚。作品不在多,而在能站立得住。要当有风格的作家,不能甘当起哄凑热闹的作家,不充当摇旗呐喊小卒的角色。”[1]这里的崇高也是“边缘”的另一种解释,是时代责任感、家国情怀内涵的另外一种表达,是特定情势下的自觉坚守。孙犁的作品与思想既对时代有超越性的知解,也有不顺应潮流的保守,看似不与时俱进,实则正是孙犁创作个性与艺术追求的体现。徐光耀在《不读孙犁,你怎么能长进?》一文中说道:“我相信,尽管古人说过‘大道低回’,但大道不会永久寂寞,世事推移,文学终将回归国风之正。”[2]“国风之正”,正是孙犁在“边缘”中守持的可喜收获。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