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京城”的文学书写
第一节 北京城的空间与文化特性
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殊性,这个特性往往会成为这座城市的标签,构成着人们对于它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就像上海的洋气精致,西安的古朴悠远,苏州的温婉安逸,成都的火辣悠闲……而北京这座城市,似乎很难简单地为它贴上一个标签。正如学者赵园所说,形容北京城用“亲切近人,富于情调,个性饱满以及所有其他概括,都显得空洞而浮泛。”①北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始终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它自身就构成着一种抽象的符号,它的特殊性就是其最大的特性。在这特殊性之中,必然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一、大而方正的空间布局
易中天在《读城记》中说道:“北京的气派,一言以蔽之曰‘大’。”②北京无论是对于中国而言还是放眼世界来看,它都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据《北京统计年鉴 2018》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市共包括 16 个区,总面积达 16410.54 平方千米,在中国城市面积中排名第六位,容纳着约 2154.2 万的常住人口。全市共有 152 个街道办事处,143 个建制镇,38 个建制乡,3209 个社区居委会和 3915个村民居委会。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北京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北京城不仅空间大,其城市布局也十分规整,呈现出方正的空间特征。元代以前,北京城的发展中心与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异,元朝定都大都后,将城址进行了转移,以金代离宫太宁宫附近的一处湖泊为整个城市设计的中心区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城市中心的雏形。元大都的宫殿设计均坐北朝南,城中有一条明显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大内”(紫禁城的前身)的中心,显示出了古代城市建设的核心思想以及封建王朝统治中心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由此奠定了北京城“方正”的城市空间布局。之后明清时期的紫禁城,便是在元大内的基础上发展改建而成的。但明代在进行改建时将紫禁城进行了南移,并结合地理、风水、气象的内容对城中的布局进行了修改。清代几乎完整地保留了明代遗留下来的宫殿等建筑,也未对于城市的布局进行大肆调整,而是将城市改造的重心放在了北京西北郊的园林开发上,“三山五园”便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城市建设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被确立为我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依旧在原来的基础上,以紫禁城为中心,沿着城市中轴线向周围四散开去。一条条正南正北的街道、胡同又将城市空间切割成一个个规整的块状区域,使北京的布局呈现出齐整之感。正如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像北京设计得这么方方正正、匀匀称称的城市,还没见过……瞧,这儿以紫禁城(故宫)为中心,九门对称,前有天安,后有地安,东西便门就相当于足球场上踢角球的位置。北城有钟鼓二楼,四面是天地日月四坛。街道则东单西单、南北池子。”①方正的布局让方位在这座城市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因此北京在为胡同、街道等命名时常在其中加入东南西北这样的方位词。这不仅为辨别方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极大地增强了北京人的方向感。
...............................
第二节 北京城市书写的文学传统
城市是在人的活动中逐渐发展而来的,同时也是被作家们的书写建构出来的。城市在文学书写中也密切参与着作品的创造,为作品赋予城市的精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历来都有城市书写的传统。而北京作为一座极特殊的城市,对于它的书写一直都在延续。文学作品中的北京不断为人们塑造着先于个人经验的北京形象,而北京书写中蕴含着的北京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又能使北京文化形成向外辐射的态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于北京城市书写的文学传统是由老舍开启的,之后的萧乾、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等作家,延续着老舍京味文学的路径,创作出了一篇篇极具神韵的京味文学佳作,并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了京味文学这一文学风格类型。京味文学“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时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借助具体的北京人情风俗、通过回瞥方式去体验到的一种地缘文化景观。”①只有“在北京场、讲北京事、有北京风、用北京话、呈北京性”的作品才能称之为京味文学。由老舍开创的京味文学有着专属于它的特征,但北京书写的范围却可以无限扩大。尤其是在社会进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外乡人也大量涌入北京,这一时期北京书写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内容不断跳脱开传统的胡同北京,走向了高楼林立的都市北京。但文本中所展现的内容依旧蕴含着浓厚的北京风味和对于北京的城市体验与想象。
“北京对于写京味小说者,可以并非‘乡土’。”①“乡土”作家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丰富的北京生活经验和文化基础,而异乡作家也能够在接触北京城的过程中把握这座城市独到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视角。在北京书写的作家中,老舍、陈建功、冯唐等基本上都是自幼生长在北京的“原始”北京人,而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等作家相对而言属于这座城市的异乡人。文学书写中城市的形象往往基于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想象与体验,带有极强的个人立场和文化逻辑,城市中“原住民”与“异乡人”对于城市的体验与感知必然有所差异,北京城市空间在他们的书写中便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选择。
..............................
第二章 顽主的“游乐场”——北京的日常生活空间
第一节 游荡——北京的街头、胡同与居民楼
街头、胡同、大杂院是存在于北京城中极具典型性的一类城市空间,也是京味文学中最常出现的文学书写空间。无论是老舍、邓友梅笔下的落魄旗人还是刘心武、陈建功书写的新时期北京中下层民众,他们的生活始终都没有脱离这个空间。而作为京味文学第三代作家的王朔,虽然他完全颠覆了过去京味文学的书写风格,但他的顽主们却依旧没有跳脱开这类日常生活空间,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将一些大杂院变成了居民楼。北京的街头、胡同与居民楼到了王朔这里,已经不再饱含历史的沧桑与邻里的温情,而是为顽主们的游荡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空间,供这些游荡者将“街道变成了居所,他在诸多商店的门面之间,就像公民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那样自在。”①王朔笔下的北京城也正是通过顽主们在街头、胡同和居民楼的游荡间建构起来的。
《顽主》的主人公杨重、马青、于观三个青年经营着一家替人办事的 3T 公司,但实际上做的却是“一点正经没有”的买卖。“每天去大街上吊膀子,当代用券。”①他们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街头,每天走街串巷,在街头代人约会,或者游荡到居民楼中,替人挨骂,做的尽是与世俗伦理格格不入的事情。顽主们在游荡中表现出了对于一切都毫不在意,随意挥霍金钱,任意处置情感的倾向,但这种随意的空间游走行为实际上却表现出当代人精神上的无根导致的游离现象。杨重在大街上替人与女友约会,一个百货公司手绢组长,一个街头小痞子,两个人却在聊人生,聊现代派,谈尼采,还要用弗洛伊德过渡,而杨重的一派胡扯却将刘美萍骗得团团转。另一边的马青,正在居民楼中替少妇不负责任的丈夫挨骂,以满足少妇对情感宣泄的需求。当马青对着少妇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时,少妇立刻收起她不满意的姿态,
“好啦好啦,到此为止吧,别再折磨你了。”少妇笑得直打嗝地说,“真难为你了。”
“难为我没什么,只要您满意。”
“满意满意。”少妇拿出钱包给马青钞票,“整治我丈夫也没这么有意思,下回有事还找你。”②
城市中不同的人花钱请 3T 公司的人来帮自己做事,这给了于观、杨重、马青三人看似正当的理由,游荡于城市的街头和居民楼中,用他们侃大山的功夫来游戏人生。他们利用自己善于在城市中游荡的本事,满足不同城市空间中人的精神需求,这不仅让雇佣者的心灵得到了满足,也使得顽主们通过在城市中的游荡填补了自身精神的空虚。他们对于未来的未知与迷茫被这种游荡及在游荡中衍生出来的各种事件一点点冲淡,这种游荡行为实际上是对于自身精神上的麻痹。而雇佣者则以虚假替代的模式,得到了情感的宣泄和精神的寄托。这都体现出现代社会中人精神无以寄托的现实。在《一点正经没有》中,顽主们不再经营 3T 公司,“‘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③于是他们成立了“海马编辑部”,集体进行文学创作。
................................
第二节 拆解——北京的公园、广场与礼堂
由于北京城市空间的特殊性,很多带有政治严肃性和文化符号意义的城市空间与市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形成了重叠,因此在顽主们通过游荡建构属于他们的城市空间时,这些空间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地盘儿。顽主们玩世不恭的行为与这些充满着政治文化意义的空间相结合,体现出王朔有意无意间对于北京城市空间中的政治意味和文化内涵的拆解。
公园和广场是一座城市中必不可少的供市民消遣娱乐的空间。而北京由于其悠远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地位,这座城市中的公园与广场在承担着休闲功能的同时,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与文化内涵。但王朔却经常将顽主放置在这样的空间之中,以“混搭”的方式完成他的谐谑。在《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中,张明是一个每天在北京城街头和旅馆中游荡,靠诈骗为生的街头小痞子,当属品行最为恶劣的顽主之流。公园即将举办晚间音乐会,张明准备通过等别人送票再卖出去的方式谋得钱财,因此他进入到了这个公园空间。这是一个有着高大、油漆剥落的廊柱和汉白玉石台的公园,在这里他遇到了吴迪。由于张明的窥视,吴迪主动与他交谈,张明痞子式的行为却吸引了单纯的吴迪。这是一个充满着文化气息的公园空间,公园里在举办音乐会,身处于这个空间中的吴迪在阅读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张明的进入和两人之间的交谈打破了这一空间的和谐。
礼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空间,承载着丰富的城市功能。会议是礼堂的原始功能之一,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表彰会、批斗会、欢送会、演讲会以及各种级别的政治会议,均在礼堂中进行,因此礼堂在城市中属于较为严肃的空间。王朔的作品对于礼堂空间也有涉及。《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中,吴迪在去礼堂参加“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的路上遇到了张明,当张明和方方进入到这一专属于学生的空间时,空间的和谐立刻被打破。“演讲会一开始,第一个女工一上台,我和方方就笑起来……等到一个潇洒的男大学生讲到青年人应该如何培育浇灌‘爱情之花’时,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已明显异于听众不时发出的会意的笑声。”②顽主不同于大学生,他们对于一切严肃的形式都心存鄙夷,否认一切激励人心的力量。他们属于这一充满着正气与朝气的空间的闯入者,同时还是用痞子式粗俗的语言和行为将空间内和谐打破的破坏者。通过这样的方式,王朔将正统的意义全部拆解。

论王朔作品中的北京城市空间
第三章 顽主之“根”——北京的大院空间....................................37
第一节 北京大院的兴起.............................................37
第二节 北京军队大院空间的公共性............................................40
第四章 城市空间与王朔的自我追寻..............................53
第一节 王朔书写空间转变的契机........................................53
一、社会文化空间的变革................................53
二、为自己正名......................................56
结语............................................66
第四章 城市空间与王朔的自我追寻
第一节 王朔书写空间转变的契机
一、社会文化空间的变革
1976 年高中毕业后王朔进入军队服役,四年后退伍回京。王朔入伍的这四年,恰是中国社会空间发生巨变的一个时期。改革开放的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以及接踵而至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使得过去中国社会空间中弥漫着的浓重的政治气息大大减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自 1949 年开始国家精心经营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空间形式逐渐消解,代之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中国。北京作为过去政治中国氛围下营造出来的“圣城”,其身份由于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就此消解,但这座城市的政治意味已然被经济气息所冲淡。军队的现代化改革也随着改革的大潮而来,对于军人的优待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军队大院相对于外界其他空间的绝对优越性也随之减弱。评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再是唯政治论,经济条件被看作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响应国家政策,纷纷下海经商,并在“遍地黄金”的社会转型初期赚得盆丰钵满。而王朔在这之前以“共和国未来接班人”的身份,怀着十足革命的热情进入到了人民军队之中,当他从军队中退伍时却发现中国的社会空间已经不再由他们做主。虽然王朔的确按照构想在中学之后进入到了军队中,但事实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成为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①便已经被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②所取代。复员后的王朔,“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越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迅速向前冲去的头晕目眩……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③时代的变革不仅没有给这些大院子弟任何缓冲,甚至直接将他们变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但作为在北京军队大院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王朔身上带有最典型的大院子弟的特征——浓重的权力和等级意识,且这种意识内化为他的品格,成为影响其最为深远的一股力量。因此,当王朔从军队重新走入社会空间时,无论是对于社会空间的巨大变革还是面对着自己身份的失落,他都是难以接受的。但这时王朔的身份又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他在应该接受教育的年纪并未专注于学习,高中毕业即入伍的他自然也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当时的社会对于知识文化的注重愈发明显,这让他难以融入到知识分子们的精英阶层中。大院空间留给王朔的权力意识又让他不愿接受自己从革命的接班人变成与普通市民无差别的医药公司业务员。“我过于倾注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一旦失去,简直就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从高处、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我很彷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④在这种对于未来的纠结之中,王朔这类人最终只能成为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多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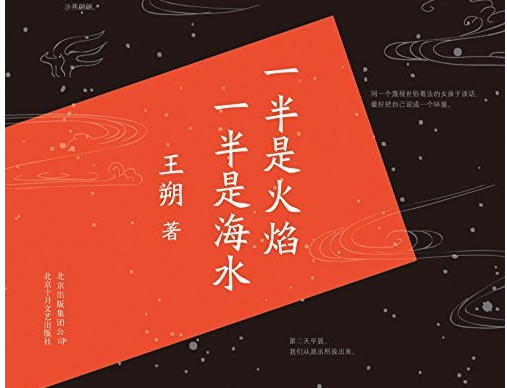
论王朔作品中的北京城市空间
...............................
结语
文学与空间始终是相互交缠着的,“文学自身不可能置身局外,指点江山,反之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本身成为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①在王朔的创作中,人物始终都是与城市空间交互存在的。
王朔作品中的北京城市空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最常涉足和生活的街头和大院,在这两类空间塑造下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性格习气也深深地篆刻进了王朔的骨子里。因此当王朔想要靠写作来谋生时,书写生活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小痞子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插科打诨、游荡玩乐的生活是王朔再得心应手不过的了。但王朔有着自己的文学追求,同时在书写与生活之中也越发地感受到以“痞子”的方式生活最终只不过是简化生活,逃避责任的手段。因此王朔开始将目光投向军队大院,以书写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来探求“我”何以成为“我”的问题。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更迭,军队大院早已失去了它们过去的形态,随之而来的便是在空间塑造下形成的王朔那一代大院青年最熟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消逝。在这种空间构成下,王朔这类人的“根”便失去了实体,只能成为一代人追忆的内容。最终,王朔在现实的缠绕与追寻之中发现了内心,并开始向更加深广的内心空间探索,去思考形而上的问题。但从王朔后期所创作的《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等作品便可发现,他最终也未能探求到真正的自己。
正如王朔所言的,他想要的太多。从最初写文以谋生,到开始在作品中思考自己、人类与宇宙,王朔的书写始终都脱不开他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也正是王朔这一类大院青年在时代变革中的缩影。在城市空间中成长、游荡,之后不断地怀念他们的精神故乡……但最终王朔依旧未能建构起足以支撑他们未来的空间,更难以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终成为了一代精神上的流浪者。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