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叛线性的失序美学
一、非匀速诗意体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代昼夜的分界点以日出日落为标志,现代科学则将时间的划分精确至秒。科学将时间的流逝切割成均匀的段落,心理时间却并不遵循这一规则,人们“记得(而非预见过去)、预见(而非记得)未来”的“心理学箭头”①,解释了时间不对称感受。西方计时、历法普及后,现代人默认接受了时间的匀速、单向的说法,诗歌时间的不均匀冲击了人们在庸常生活中的神经,在这个缝隙里,诗美诞生了。
李元胜多次在诗歌中明确提出诗歌时间的独立性和失序特质——“至少,时光不应该是匀速的/有些年可以快进,有些天可以一过再过”(《略有悔》),《给》一诗也言明梦境中创造的世界是悬空于时间之外的,现实时间为主轨,梦境是悬置其上的平行轨道,而诗歌时间是断续镶嵌于主轨的千万条旁支,共同构建起血管状庞大的体系。错过的时光并未消逝,“仅仅拐了个弯,在岁月另外的层面上/和我们一起前行”“无数昔日之我,无数张纸片一样叠出今日之我”(《习惯在余烬中继续》),诗人对于时间与“我”的关系有相当清晰的界定,也就意味着其主体有着高度的时间自觉意识。
李元胜诗歌世界的非匀速诗意体验的基本构成,是由快镜头、慢镜头、瞬时、停滞、永恒、脱离等艺术手法共同构建的。在具体文本中,一个下午,可以“无数日出日落交替”(《嵩山之巅》);一个春天,可能“需要几十万年的缓慢”(《无花果》)。时间会“以崩溃的速度运行”,李元胜把“终日阅读的人”比作“过度使用的刹车片”,以全画幅高速运行的画面完成被追逐着消耗的人生景象(《景象》)。
..............................
二、折叠的时间:裂罅之美
《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柏格森提出曲线比断线优美的缘由在于,曲线“每个新方向都被前一个方向指示出来。这样就发生了一种转变:原先我们在运动中看见;一转变,我们掌握了时间的川流,在现时中把握住了未来,因而感觉愉快”①,这种心理预期的满足带来的完整而绵延的美感体验,顺理成章地为大众喜爱,而断线的所呈现的破碎与非秩序状态则并不符合常态的审美预期,这也是传统诗学讲求“行云流水”与圆融美学的缘由。李元胜反其道而行之,对普遍的审美心理进行突破,摸索出新的诗歌美学——裂罅美学。所谓裂罅美,是对完美整一的反抗,李元胜诗中随处可见伤口、创口、裂缝等意象,在其沉静文字的水面下情感的波澜就从这里涌动,如同瓷器釉面形态不一的龟裂,诗人正是用这些伤口构建出诗中之“我”的灵魂。
早在创作初期,这种生命的裂痕就投射在诗歌中,1990 年《乌鸦》一诗有对夏季“最简单的伤口”的画面模拟——“哭泣的孩子穿过田野/想着一个名字/一只乌鸦在他的前面飞着”。随着写作与人生经验的丰富,“伤口”褪去了青春感伤式的氛围,逐渐变成李元胜诗歌的一个标志。
李元胜的诗中,伤口似乎是一个万能喻体。“一首未写完的诗,像一个缺口”(《丁山湖的早晨》)拥有黑洞一般神秘而强大的力量。诗人也将自己看作是一条裂缝——“我知道自己的狭窄/像一条深深的裂缝”,但缝隙并不意味着空洞,而是透过写诗之人的这点裂缝,向世俗洒下一些光亮。此外,李元胜常常把花朵比作伤口,“当一场小雨/全部落进某个伤口/缓缓松动的花正打开天堂”《观蝶》;“我的李花已落,山矾像新鲜的伤口/香气披头散发”(《铜铃山半日》);“秋天,一切不过是柄刀/暗中挥过/百合带着伤口坠落”(《绘有人物的瓶》),花苞圆而有缺的伤口是绽放的契机,等待着于伤处发现美丽的慧眼。
..........................
第二章 心理重构的时光笔记
一、生命体验为标尺
真实世界的时间并没有永恒统一的度量衡,而诗歌宇宙的时间秩序却由创作者一己裁定。在这个世界中,诗人的心理时间是唯一准绳,个人的经验是搭建的世界的材料,正如李元胜自己所认识到的——“正是我看到的,听到的/堆积起来,构成了我的心灵”(《给》)。
“诗是经验”是诗论的老生常谈,这一提法是针对传统的“诗是情感”观点而言。早在新诗诞生初期,胡适就在《梦与诗》中提出“诗的经验主义”,表明“做梦需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批评“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①。“诗的经验主义”更为著名的倡导、践行者当属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小说《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中,里尔克提出:“诗并不像大众所想象,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②梁宗岱、冯至、徐迟、穆旦、绿原等众多中国诗人都曾深受这一经典诗学主张的影响。
李元胜的诗歌之路,也是从接触里尔克的作品后开始的。里尔克的《秋日》震撼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李元胜,据诗人回忆,自己将冯至译版《秋日》抄下来仔细推敲品味,随后激发了模仿创作的念头。不只是诗歌创作,作为源头性的影响者,里尔克的经验主义也潜移默化着李元胜的诗歌理念。在李元胜为数不多的论诗文章中,“经验”是其理论的核心元素。《诗歌是一种资源性的写作》一文中诗人提出诗歌区别于小说、散文的文体特质:“它依靠语言的复杂性,来表达出某个时代的幽微和独特经验”,足见得李元胜诗歌的“血与肉”,一是语言,二是经验。随后他又指明“有限的文字中,要表达全新的经验,必须有与之适应的全新言说方式”,“清醒于寻找线索时的警觉,沉醉于所有素材——那些经验的复杂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使用了语言的工具 ,用它来撬开已有的窗甚至凿出全新的。”③语言为适应经验而存在,为经验服务,一切生活经验都可能进入诗歌,诗歌来源于生活却低于生活,由此形成了“生活——经验——诗歌语言”的层级模式。在现实生活和形而上艺术之间,“经验”是转换和生成的机制,暗含的是对人主体性的极大肯定。回忆重组后再现的人生经验,要求诗人要将自己所感知的一切存在与自身融为一体,体现的也是一种冷静、沉着的创作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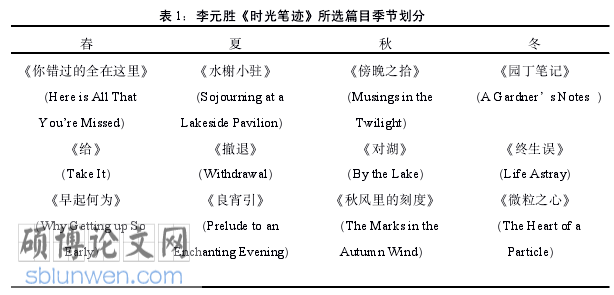
文学论文参考
二、个人化的时间意象
成熟的诗人大多拥有自身独特的意象系统与标志性的意象,屈原有“香草”“美人”,穆旦有“野兽”“肉体”,海子有“麦子”“水”“太阳”等代表意象,根据这些典型意象,即使没有深入阅读过该诗人的作品,也可以大致领会到诗人的创作倾向。这种独特性并非依靠意象本身的新奇程度,而是意象在整个文本背景中综合被赋予的个性特质,以此传递着诗人的内心结构和审美理想。
汪静之有一首作品——《时间是一把剪刀》,把生命比作“一匹锦绮”“一树繁花”,而时间是“剪刀”“铁鞭”,把美好剪断、击落,还要付之一炬或是践入泥土中。汪静之的时间意象,突出的是时间的残酷性,对美好的摧毁力量。由于一直尊崇“旷野的诗意”,李元胜诗歌的时间意象大多脱胎于自然,而放逐“钟”“表”为代表的标准时间意象,即使斥责时间无情,文字也大多安静沉稳。《一生》中两人分别后,钟表里便再也看不见“因为爱而惊慌失措的脸”,或《平衡》一诗“钟表”的斤斤计较无济于事,爱与厌倦仍在消耗着我们的生命,无力感都胜于痛斥感。
无论是《寻茶记》中表明的“我和所有事物保持着时差”的态度,还是 2020年 1 月所作《给》中,“它像一个抬腕看表的人/只不过,使用的是另一种时间//就像我路过它,你用日记写到它/而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钟表里”无路可循的而又无力挽回的隔膜感,钟表作为标准时间的意义在李元胜的诗中都被架空。又或如《沉默的钟》里出现的三种“钟”:一是被无人敲响的银制旧钟;二是我们背负着的“无人知晓的巨钟”;三是隐藏在自然中植物被风刮过的发出声音的“钟”,立足点依次由实物本体,向人类,再向无尽时空中渺渺的众生推进。最后,诗人提出了三个问题,即钟何时敲响?敲钟人是谁?谁能承受成千上万口钟的巨大轰鸣?对于事物本源的追问,让“钟”与钟鸣逐渐脱离了单纯报时意义,其广阔的视野和对万物细微的悲悯,可谓“一粒沙见宇宙”。
李元胜诗歌丰富的时间象征之中,虽然有诸如“时光就像一架巨大的钢琴”(《我需要》),“如果时间穿过我们/好比流沙穿过沙漏”(《某个夜深人静时刻》)这类意象,但更多的是充满田野气息的意象:“白昼是上升的树”《昼夜之间》;过去的一切是“被遗弃的蝉蜕”(《黄昏》);“剩下的时光,就像一根旧绳子/还来得及,让我们扎好一切/让他们具有稻草垛的秩序和形状”(《六月醉书》)。在此之中,“蝴蝶”与“花”,李元胜又尤为偏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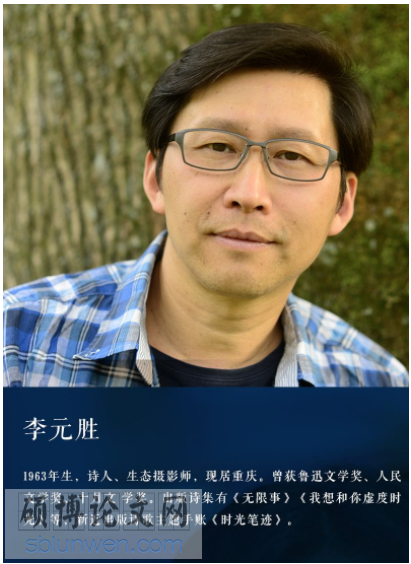
文学论文怎么写
..............................
第三章 时间困境与诗性超越................................ 35
一、 “纸质的时间”:作为介质.....................................................35
二、循环时间:消解崇拜与恐惧.......................................... 38
三、“虚度时光”:抵抗时间暴力.....................................40
结语.............................................. 47
第三章 时间困境与诗性超越
一、“纸质的时间”:作为介质
李元胜诗歌的时间意识最大的意义所在,即是消解崇高,破坏近代以来进化论塑造的的时间神话,为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劫持已久的现代人松绑。时间在形而上学的意义越神秘崇高,越是诱惑诗人们把它装在一个有形的笼子里。博尔赫斯说“时间是我的构成实体。时间是一条令我沉迷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时间是一只使我粉身碎骨的虎,但我就是虎;时间是一团吞噬我的烈火,但我就是烈火。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②。河流、虎、烈火的象征,是诗人对时间与存在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的转换,诸如废名《无题》 “在赴死之前得到解脱,于是世间是时间,时间如明镜,微笑死生”,以及昌耀《旷原之野》“一切是时间。/时间是具象:可雕刻。可冻结封存。可翻检传阅诵读。……时间是镶嵌画”,时间具象的差异,乃是诗人思想与想象多元的碰撞的结晶。
时间可以幻化成世间万物,但在李元胜的诗意世界里,它是的特性是由“纸质”彰显的。李元胜的纸质时间并非指向其轻、薄的特性,如《致读者》中所言——“光阴教会我的东西/对于纸张永远不会太轻……那么这就成为可能/我在秋天无意的落叶/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你们的春天”,以“纸”为介质构建的文字时间,将文本、阅读、写作视为与时光、历史的沟通方式,达成了化无形为有形之效。李元胜说自己偏爱开放式的写作,“生活中所有的经验都可能进入我的诗歌”③,然而人生活的视野和长度毕竟有限,纸质的时间乃是对个人经验局限性的突破,写诗的意义不单在于揭露普通的事物的光芒,还能“同古老的手无意相触”(《每年都应该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相触的手实质上超越了“我”的人生,进入他人的时间领域。同样的观点在《阅读的时候》中也有体现,“我”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去经历他的经历,甚至直接摘取他思想的果实。《每首诗都是井口》更进一步说明了纸质时间对接的方式,即我们望向不同的井口,亲近的是“身体中有相同火焰的人”,内心深处脉脉相通的东西吸引着两条时间轨迹重合。
............................
结语
“时钟敲响着召唤每一个人,/人们直看进时间的底蕴”①,里尔克指出了时间无可抗拒的魔力与意识对行为的召唤,但“看”的动作之后,诗人并没有给出底蕴的答案。本文拆解李元胜的时间意识为反叛、重构、超越三个动作呈现,将意识化解为艺术行为进行观察研究,这一方法论的选择基于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启发,也是基于时间、意识、诗境话题的三重抽象性特质。在创作手法—诗人意识—诗人行为的链条之间,虽然文章部分涉及李元胜田野调查等生活行为,但主要聚焦于时间意识与诗歌艺术的第一重关系纽。
蒋寅曾提出最能代表中国人时间意识的诗人是李白、杜甫、苏轼,认为“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人时间感觉和表达的三种模式……反抗时间、顺从时间、超越时间三种透过时间观念表现出的人生姿态"。②李元胜的“虚度”与“浪费”可以说是三种模式的现代综合,在反抗中完成自我复位达成内在超越。相较于古典诗歌,新诗中的时间意识的“新”不仅体现于时间意象与附着情感、意义的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在商潮滚滚,“娱乐至死”的加速度时代里对处于隐形暴力下的人的生存命运的关注与关怀。李元胜“纸质的时间”与“虚度时光”,都是在此意识下抵御时间暴力与慰藉精神困境的路径。
访谈中李元胜说自己写作的方向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探测存在”,诗歌是一种特别的日记,希望“通过写诗找到生活的意义,通过写诗来理解生存,理解生与死。”③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李元胜的时间意识并不是围绕某个核心观念一成不变,而是在怀疑、分裂、混乱中逐渐摸索何为好的人生、好的时光。
博尔赫斯诗中之问,以期后来者解答。
现世之读者,或可借李元胜纸质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