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抒情传统”的观念生成与历史传承
1.1 抒情与文学:“抒情传统”的时代演进
以往的文学研究认为,“抒情”是创作个体的感时伤逝。相对于现代以来以“启蒙”和“革命”为主潮的文学观,“抒情”更被看作是个体与宏大历史的背道而驰,是小资情调和个人的情感滥觞。不同于西方文学中,“抒情”是个人情感的呼喊和自我个性的张扬,中国文学的“抒情”将个人情感和民族国家相连接,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伦理性。“抒情”文学因此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都和国家民族及道德伦理难以分离。由《诗经》楚辞延续下的“抒情传统”一直在中国文学中流动并产生深刻影响,并在八十年代再次实现对政治运动时期被压抑的纯文学式的“抒情传统”的接续。
1.1.1《诗经》楚辞时期:古典“抒情传统”的形成
诗歌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和精神气质。《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开端,明代杨慎就表示“《三百篇》为后世诗人之祖”。先秦时期诗乐舞之间紧密结合,《诗经》亦是。《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篇”①。朱光潜《诗论》从诗“重叠”、“和声”、“格律”、“韵”等方面考察中国诗歌,认为《诗经》中重章叠句、“兮”的词语、音调重复的现象均是音乐性的表现,论述了古典诗歌诗乐舞间的关系。②由此,陈世骧依据诗词的“复沓”和“叠覆”,探究了中国抒情诗具有“反复回增”的特点,认定“兴”是《诗经》抒情性表现,也是中国诗歌抒情性的核心。①《诗经》中描述的内容大多很简单,基本围绕在生存、爱情、劳动等基本活动,为读者提供了精神向往的田园世界,并抒发了人民最真挚、淳朴的感情,以其音乐性和抒情性开启了中国抒情诗的发展。孔子以“思无邪”评价《诗经》,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使儒家从政治教化的角度解释诗的作用。在情感的表达上,孔子受到“中庸”思想的主导,认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赞美其“温柔敦厚”的抒情风格,希望文人可以体会到世界真情至理又能在表达时有所节制,达到修身养性的目标。至此,情感“含蓄”的文学风格成为传统文人创作追求的艺术境界。
............................
1.2 抒情与个人:汪曾祺的文学观念与内在追求
汪曾祺被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和他的“抒情”气质是分不开的。出生在文人家庭的汪曾祺幼时就学习古典文学,并深深的沉浸其中;而生长在高邮水乡,也使他同淳朴生活融汇在一起。总的来说,家庭生活,学习经历和成长环境都决定了他是一个诗人式的小说家,具有“烟火气”并表现出亮丽的生活气息,带有“抒情”的风格和文学传统。
1.2.1 对闲话抒情文学的欣赏
汪曾祺出生在一个士大夫的传统家庭中。汪曾祺的祖父是中过举的拔贡,在汪曾祺童年就教授汪曾祺《论语》、八股文。祖父对孔子的讲解虽然并不能完全被年幼的汪曾祺理解,但汪曾祺感受到了其中的“气氛”,也可以说这奠定了汪曾祺之后对孔子仁爱的理解和赞赏。汪曾祺的父亲为人和善,多才多艺。生活中,汪曾祺的父亲极具有闲情逸致,会做各种手工,会演奏许多传统乐器,是运动强将,与和尚交往不拘约束,还喜欢各种图章字画。祖父和父亲的影响浸润了汪曾祺的性格和思想,让他对传统文学产生兴趣和热爱的同时,形成了温文尔雅的性格和柔和温润的文学视角。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离不开他本人的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
汪曾祺认为,“一个人的风格和他的气质是有关系的”,“要形成个人的风格,读和自己气质相近的书”“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口味的书”。①汪曾祺赞赏和喜爱的作家作品,古典文学中归有光首当其冲。汪曾祺多次表示,自己喜欢归有光的散文,认为归有光文章能够做到平易自然,结构上松散无拘,却在简单的表述中阐发深刻的情感。《项脊轩志》是汪曾祺不断回味的短篇,尤其是对于归有光在文章前半部分平淡却又精简的叙述大加赞赏,认为归有光的叙述方法,值得当代作家学习和借鉴。
2 传统的接续:汪曾祺对“抒情传统”的继承
2.1 受“抒情传统”影响的审美观
汪曾祺自己认为,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他从小看父亲的绘画有脱不开的关联。生长在传统文人式的家庭中,使汪曾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个作家的根本的审美观,还是要从民族文化中获取,受民族文化的滋润。汪曾祺正是从传统文化的审美中滋养自己的审美观念。
2.1.1“静观”说:“无事此静坐”
“静”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哲学理念。“静观”是主体对事物真理把握的重要方法。道家主张“虚静”,老子就提出因为道的不确定性而应“致虚极,守静笃”,致极守静感受“道”;庄子更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主张通过绝对的“虚静”体悟道,即“坐忘”“心斋”等方法,达到主体与“道”合一,通于万物的境界。在宗教中,“静虑”成为信徒修行参悟的方法。在儒学思想中,君子需要“静定”内省,修养道德品质,提高自身境界,体会物我同一的生命意义。新儒家学说中,仁者往往在对宇宙万物的“静观”中消除了物我的间隔, 同天人而合物我而缘情起兴 ,有一种自得于心的洒脱。②总的来说,古典文学中,创作主体通过“心斋”等方法体悟世界,提升境界,在艺术审美中表现为对空幽意境的不懈追求。
幼年时的汪曾祺经常在外祖父家安静的屋子中静坐看书,并对屋中所挂“无事此静坐”的横幅十分欣赏,也形成了他“静”的品性。汪曾祺回忆那段时光给自己定下结论是:“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一点隐逸之气”。静坐的习惯在晚年时一直延续着,汪曾祺经常在早晨,伴着一杯茶和一支烟,快然独坐,浮想联翩。汪曾祺的儿女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静坐出神。儿女们知道,每当这时,也是新作品正在酝酿的时候。汪曾祺好“静”,并在“静观”中延续了儒家“不累于一切”的“自得之乐”。
汪曾祺多次在题画和书法中提到对“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赞赏。汪曾祺将他的人生态度表现在他的绘画中,至此他笔下的菊花不再是陶渊明笔下遗世而独立的隐士,而以“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展现了一个中国传统抒情式文人的“静观”景象,形成了“佳兴”与主体的“同”。正如他自己所说,“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①。
.........................
2.2 受“抒情传统”影响的创作观
在创作上,无论是“抒情传统”中的“言志”还是“缘情”的观念,都在他小说中延续下来。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新文化运动的接续者,国家和民族是创作中不可缺少的话题,对人的关注,更成为其创作的核心观念。而“情”又是文学创作的冲动来源。“作家就是产生情感的”,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汪曾祺对“抒情传统”的延续。
2.2.1 对“诗言志”:小说的“兴”与“怨”
“兴”和“怨”是“诗言志”表达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儒家的诗教理念中,“兴”“观”“群”“怨”是诗歌功能和认识作用的重要理念。《文心雕龙》中写道“兴者,起也”,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朱熹解释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①。同时,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情感、理智的启发,“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在技巧使用中形成“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文学意味。“怨”可追溯到屈原“发愤以抒情”,更指涉一种“不平之气”,“不平则鸣”,是作者失意不遇的情感排遣。王德威认为,作为诗教说的两端,“兴”和“怨”之间在情感表现上具有很强的张力。王德威指出现代是一个“兴”的时代,但是文人感时忧国、独立苍茫的怨离之情又凌驾于其上,成为创作的前提。②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唯有‘兴’的发动创造能力,才能有气象一新的诗情或者壮志;但也惟有其有了‘怨’的意识,抒情主体的发声方式就不仅是纯粹自然的创造,而是有了对历史——及其所带来的不安和不满——沉重负担的回应。”③“兴”和“怨”作为诗教传统,可以促使作者将外在经验内化为一种情感,最终以比喻、象征含义的修辞手法传达作者情感或实现政教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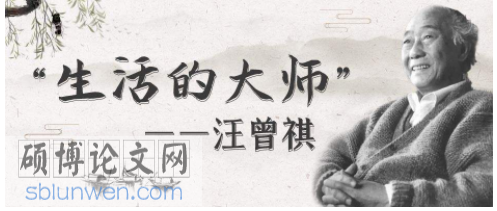
文学论文参考
3 本质的回归:汪曾祺对“抒情传统”的创化......................................30
3.1 中西融汇:西方文学与“抒情传统”的结合............................... 30
3.1.1 化解冲突:西方悲剧观和儒家思想的“和谐”................................. 30
3.1.2 艺术同构:“空白”理论的时代新质............................ 32
4 汪曾祺对“抒情传统”继承创化的历史反思.................................43
4.1 观念创新:汪曾祺抒情小说的文学价值................................... 43
4.1.1 对小说抒情主体形象的强调......................................... 43
4.1.2 对“文体变革”热潮的呼唤........................................ 44
结语....................................50
4 汪曾祺对“抒情传统”继承创化的历史反思
4.1 观念创新:汪曾祺抒情小说的文学价值
陈思和表示,汪曾祺小说创作手法使中国文学将出现分化:从社会化的文学转向个人化的、审美化的文学。这种文学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文学创作。①足以见汪曾祺抒情小说对八十年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在抒情主体上,汪曾祺小说将抒情主体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并发展了现代文学上士大夫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抒情主体;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其抒情小说对八十年代中期“文体变革”的产生积极呼唤。
4.1.1 对小说抒情主体形象的强调
中国人的“视野”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论,只有唯“天子”为上的人生观。②因此,在古典文学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自我的觉醒。作为对内在经验进行阐发的抒情主体,和社会也就密不可分,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一方面他们对社会现状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表达出强烈的反叛意识,在入世意志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被迫或自愿选择逃避,在自然中寄托人生,发表感慨。虽然明清晚期,个人意识大幅觉醒,但就古典文学的整体来说,抒情主体依旧是具有很强社会性的个人。
五四文学革命后,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呼唤和确立个人主体性。因此,此时出现了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极致个人思想表达的抒情文学。抒情主体作为独立个人,抒发个体情感的意识开始真正觉醒。但很快,社会动荡下革命风潮让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群体的重要,他们将文学创作主体也由个人逐渐转向群体,从个人抒情诗式的表达转接到所谓“史诗”性的表达。个体将意志托付到群体中,抒情主体以群体形式代替个体发言。这种模式延续到社会主义文学中并达到顶峰。一定程度上,正如普实克所认为的,中国现代文化史,是一个从抒情性到史诗性的过程,抒情主体的主观意识和个人主义,长期处于史诗主导的文化语境中。
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归来作家痛斥历史对个人造成的伤害,但抒情主体的抒情并没有真正从群体中国跳脱出来。直到 1980 年,汪曾祺因《受戒》名噪一时。在《受戒》的结尾处,汪曾祺表示,自己所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梦也就代表,这篇小说描写的内容是极具个人性的。由此,作为个体形象的抒情主体在文学作品中再次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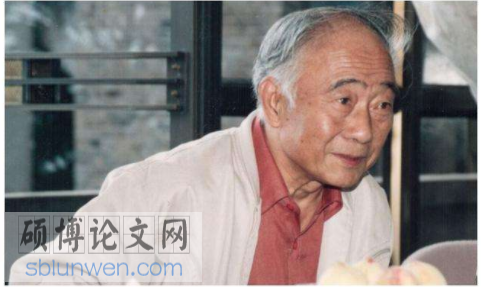
文学论文怎么写
.................................
结语
中国古典文学中,自《诗经》和楚辞开始,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质就基本确定下来了。相对于西方纯粹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言,中国文学的抒情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政治,社会,家庭,民族,血缘等多重含义。在古典文学中,形成“诗言志”和“诗言情”为主流代表的“抒情传统”。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可看作和西方史诗文学相媲美的文学荣光。王德威将“抒情传统”的观念引入了现代文学中,考察在继承了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抒情传统”的文学特质后,在革命和启蒙之外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又一面向。王德威以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指出,抒情不只是一种文学风格,更是一种生命意识、生活态度、话语模式,甚至政教观念。其扩大了抒情的内涵,增进了对小说研究的方向。
作为一个跨越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家,汪曾祺对古典文化的积累,对现代文学的传承,对外国艺术的借鉴,对浮沉人生的思考,共同促使汪曾祺小说在新时期“抒情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本文用四章的内容分别从汪曾祺接受“抒情传统”的文化背景,汪曾祺小说中“抒情传统”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汪曾祺对“抒情传统”的创化和价值反思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在“抒情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化用中,汪曾祺以中西交汇,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抒情化的文学观和创作观,形成了其小说在文学史中连接新时期“抒情传统”独特的文学地位。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