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于“非虚构”文学
1.1 “非虚构”文学溯源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有“非虚构”的写作倾向,如果将《史记》、《汉书》从纪实角度考量都具备了“非虚构”特征,这种特性在历代史书写作中得以继承。不仅古代史书中有“非虚构”传统,古代散文也有“非虚构”写作的因素,清代方苞的《狱中杂记》记录了作者在狱中的真实经历;近代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也有“非虚构”色彩;五四时期出现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非虚构”佳作,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及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等;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周韬奋《中国的西北角》、夏衍的《包身工》,“十七年”时期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及 1976 年黄宗英的《大雁情》、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都证明“非虚构”的写作特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从未缺席。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写实主义重新拉开序幕,《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是刘心武以“纪实小说”之名发表的作品,这一文学形式最终以“纪实小说”之名尘埃落定。在同时期,张辛欣、桑晔合著的作品《北京人》以“口述实录”的命名方式逐渐兴起;另一方面,《钟山》杂志社推出活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引发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浪潮,出现了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一批优秀作家,坚持写实主义原则的“新写实小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力。
90 年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了纯文学的传统地位,文学开始出现“边缘化”趋势;新写实小说因“在残忍裸露的庸常人的世俗生活形态中消解尽了意义、终止了谈判从而走到极限[1]”。因此,1993 年《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栏目,以积极引导作家的写作态度为出发点,提出作家应当“深入生活实际的各个层面,躬身去实践”,立足于自身的体验、观察和感悟,响应这一文学号召,涌现了关仁山的《落魂天》、刘庆邦的《泥沼》等优秀作品。上述写实文学的更新换代正是社会背景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两方面作用的结果,非虚构文学在 21 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并繁荣离不开文学潮流的积累和沉淀,新世纪愈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思想氛围允许作家在最大限度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由此引发了虚幻缥缈的网络文学的盛行。“在虚构丛生的时代,真实或真相已然变得稀缺。[2]”而读者和小说家达成共识的是:社会呈现出的真相有时比小说的“虚构”更令人难以置信。在“真相”比“虚构”离奇的社会现实中,人们宁可相信“谣言”,也不愿去相信“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对“真实”的概念认知,不仅仅包括了读者对它的心理期待还有情感方面的寄托。
.......................
1.2 从《人民文学》说起
中国“非虚构”写作在新世纪兴起,由各方面因素合力而成。早在 2003 年,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就对报告文学持有不满情绪,他发表论文提出“报告文学的资源已经枯竭”,报告文学作为一特殊时代的产物已经不适合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实际中存在,在叙事伦理和思想主题方面有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一方面报告文学强调客观真实另一方面又妄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值得关注的是,《人民文学》在推出“非虚构”专栏的前两个月,主编李敬泽为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策划了一场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思想”和“文学”的实质关系——“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前沿上,文学是否真的在场?”实际上这句话传递了两个内容:第一,文学是否能回应生活中那些尖锐的社会问题?第二,文学是否能积极参与社会意识的生成?在这一点上,李敬泽似乎指出了当代作家创作的症结所在:作品缺乏创造性。在 2006 年,就有不少批评家提出:当前作家建构的文本内容与中国的现实严重脱节,作家们失去了把握现实生活的能力和诚意,文学逐渐远离了对社会公众话题的探讨,文学逃离政治的束缚后又陷入了趋附市场的歧途。当前文学界对生命境遇的反思、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求等方面都甚少涉及,这些问题的核心都可以概括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2010 年《人民文学》第二期非虚构专栏刊登韩石山的自传《既贱且辱此一生》为标志昭示着“非虚构”文学在中国的正式兴起。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有部分作品以“非虚构”的命名方式问世并赢得赞誉,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作品。随后《人民文学》举办了“人民大地·行动者”的写作计划,号召作家走出书斋以行动介入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以写作记录时代的发展轨迹。杂志社又紧锣密鼓的设立了“非虚构”作品奖,获奖作品分别为《中国在梁庄》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三年后第二届“南方国际文学周”首次颁发“非虚构写作”大奖,《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中国在梁庄》分别获得历史类奖和文学类奖。此外,“话语青年作家奖”也设立了“非虚构”奖项。从“非虚构”文学栏目的设立到写作计划的广泛号召力再到评奖机制的日渐成熟,都为其日后发展做出了良好铺垫。
..........................................
第二章 梁鸿创作中的互文性
2.1 梁鸿创作中的自文本互文
自文本互文指同一位作家创作的不同文本间的相互关联,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同时,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的另一部作品,各部作品间的人物情节相互关联,使作家的创作在整体上形成对照关系,既体现了作家创作的内在贯通性,也使得文本间的指涉不断扩展、衍生出更加丰富的意义。当我们对梁鸿作品进行比较阅读时发现,在她的非虚构作品“梁庄”系列与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和散文集《历史与我的瞬间》中作者刻画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叙事手法都存在一定的相似和关联性。作为梁鸿互文性写作的重要一环,理清梁鸿作品中文本内部的互文关系,有助于我们在整体上把握其创作的风格和特点。
2.1.1 文本中人物之间的互文
人物和情节的再现是指同一人物和情节在作家的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希利斯·米勒将这种重复解释为“在同一文本中有某一事件或情节、场景或人物衍生的主题重复,以及重复另一部小说中的主题、人物、动机和事件。[1]”人物和情节的重复是梁鸿作品中最常见的互文现象。
(一)知识分子群体间的互文
在一篇创作谈中梁鸿提到“写了《梁庄》之后,我觉得最幸运的,是我在脑海里留下了很多人。……所以在《神圣家族》,我实际上缩小了场景范围。我在写一个个人。”[2]在《神圣家族》中梁鸿重点刻画了三位小镇知识分子形象:杨凤喜、明亮和蓝伟。三位主人公都接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都在体制内求生存,属于小镇中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杨凤喜》中主人公杨凤喜是吴镇唯一的大学生,从小家庭贫困、姐妹众多,他的父亲是个不甘平庸的农民,一直梦想做官,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杨凤喜身上。从小被训练各种规矩和礼仪,直至杨凤喜在大学当上学生干部的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父亲的教育是多么完整和必要。他彬彬有礼、沉默含蓄,立刻把他从许多无知的农村孩子,以及众多单纯傲慢的城市学生区别开来”(见梁鸿《神圣家族》P140)。杨凤喜确实是个才子,会拉二胡会写诗,有一双忧郁的黑眼睛,自然而然的和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张晓霞谈起了恋爱,毕业后为了做官走向仕途抛弃初恋女友娶了吴镇党委书记的女儿。参加工作以后,他一方面期待着岳父的提携也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应该是一片光明和平坦,另一方面也怀疑自己的才能和资质。最终阴差阳错地被分到学校当老师,为了自尊心从不去领工资,故事最后杨凤喜陷入了爱情和事业的双重失意中。
.......................
2.2 梁鸿创作中的他文本互文
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它文本”[2]。这就意味着文学史孤立的存在,一个文本总是向前文本“对话”的方式建构自身,对于梁鸿这种拥有多重写作身份的作家,由于长期研究中国乡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基础都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前文本。本章就“与经典作品的互文”、“与现实类非虚构作品的互文”出发,对梁鸿的创作风格和文化态度进行深层透视。
2.2.1 与经典对话的互文性
罗兰·巴特说:“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的、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1]。在乡土文学一脉相承的传统背景下,“梁庄”系列与中国乡土小说中的经典叙事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对鲁迅乡土小说开创的“离去——归来——再离去”和“看与被看”的叙述模式有所继承和创新。由此中国乡土小说的经典叙事模式和“梁庄系列”形成一对互文性文本,然而叙事模式背后所蕴含的作者的写作立场、想传达的文化内涵各不相同,这些区别恰好体现出作家创作的深度和新变以及“梁庄系列”呈现出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样貌。这一节,笔者将“梁庄系列”与鲁迅的乡土小说进行对比和参照,旨在探讨两类作品的互文关系
(一)离乡与归乡叙述模式的对比
乡土和民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描写农村和农民的小说自然形成了固定的文学传统。作家们的呈现分为两种:“一是从现代意识视角去传达一种对它有着重重糟粕积淀的落后现实的人文批判;一是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信仰时,从它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中发掘出一种与人的生命本能相关的原始正义”[2]。
鲁迅乡土小说独创的叙事模式“离去——归来——再离去”,作为一种经典的叙事模式,它承载着作者在特定社会背景和历史时期下的审美理想和深厚情感,蕴含着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建构和想象。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拓者,《社戏》、《故乡》等作品的归乡叙述模式,成为鲁迅小说创作中独特的艺术表征。鲁迅的“归乡”模式蕴含了深刻的批判思想,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发掘出深远的意义和复杂的内涵。而这样独特的叙述模式被现当代作家自觉延用并加以创造,使得归乡话题成为活水之源,一直被传承至今。梁鸿的“梁庄系列”与鲁迅开创的归乡叙述模式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同中有异,比较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可以窥见时代变迁之中,归乡叙述模式的常与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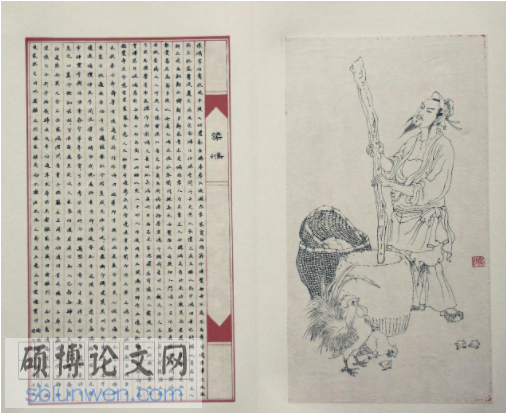
第三章 梁鸿创作中的叙事艺术...................................32
3.1 独具特色的叙事模式.......................................32
3.1.1“抗争”模式................................... 32
3.1.2“逃离”模式............................... 34
第四章 梁鸿创作中的特征与局限........................................44
4.1 梁鸿创作中的特征..............................................44
4.1.1 复调式写作的特征............................................44
4.1.2 民间话语狂欢.........................................46
结语...................54
第四章 梁鸿创作中的特征与局限
4.1 梁鸿创作中的特征
4.1.1 复调式写作的特征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认为,作者与人物之间是一种平等共存、互相交流与对话的关系。由此,“一个全新的叙事视角代替了独白式的叙述视角,进而实现了‘本文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多重复和统一’”[1]。根据层次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对话划分为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微型对话表现在梁鸿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中,这些人物彼此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使得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只间喋喋不休的相互争论着,小说因为不同声音的相互交织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复调。
《神圣家族》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叙事空间——“吴镇”,力图展现社会在历史转型时期乡镇里的人物和事件,表面上相对独立的十二个故事在深层上又互相勾连,用小人物展现时代的变化。整部小说似乎没有主人公但细读起来仿佛各个都是主要人物,“云下吴镇”由复调的结构展现并用独特的意象构建荒诞的叙事。《肉头》是一个关于一段搬弄是非引发的闹剧,讲述了在医生毅志和家人讨论邻居程林发现自己的妻子秀琴出轨的前因后果。作者巧妙地安排了“长舌妇”杨秀珍作为这次讨论的引导者,她不仅是“口舌之战”的挑起者更是吴镇所有“新闻”事件的传播者,“吴镇既是她的一盘菜,角角落落早就烂熟于心。她信手拈来,东采一点,西摘一点,烩在一起,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就有机而整体化了”(《神圣家族》第 123 页)。而在《漂流》里,毅志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乡村医生,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坐在柜台前面周而复始工作,“他一个人起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发呆,世界唯有他自己”(《神圣家族》第 23 页)。在《大操场》一文中的毅志又是一个设法买楼、机关算尽的企业家;同时在《肉头》里他是无所事事的“妻管严”、《好人蓝伟》中他是仗义疏财的好兄弟,在所有人离开蓝伟的时候只有他一直陪伴左右。另一位反复出现的人物是少女海红,在《那个明亮的雪天下午》中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放学迷路后要依靠昏暗的灯光回家;《圣徒德泉》中她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又是被疯人德泉拯救的海红;《在明亮的忧伤》里她又化身为善解人意的成熟女性。作者在不同的故事中以不同的视角描绘了同一个人,并使用复调的叙述方式结合人物互现的方法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书写过程中,作者没有直接对人物的价值观做出道德高度上的评判,而是力图展现个体意识差异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每个人物背后有他所代表的社会文化背景,每个人物都发出独立又互相融合的声音,整部小说又因为不同的声音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复调”。

..............................
结语
梁鸿在现实与虚构、过去与未来、全知与未知中自由切换,她的笔尖掠过乡村繁复的表象,走进幽暗的农村世界深处,用精确的笔法呈现出关于“梁庄”和“吴镇”里鲜活的细节和家族人物。
梁鸿最初以批评家的身份被学界熟知,其发表的学术论文具有很高的理论深度和严密的逻辑架构。而她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呈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残酷生存状态,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本文第一章将新世纪“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始末作为背景引出梁鸿的作品;她的文学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富代表意义,这种代表意义体现在她的多重写作身份上,因此,我们在第二章选择用互文性理论作为研究梁鸿创作实际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与此同时,由于互文性理论强调讨论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作家身份、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和转换,因此从互文性理论切入,对梁鸿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现实与历史、多重创作身份等关系进行分析无疑是最恰当的研究途径。依据互文性理论,我们将梁鸿作品中的互文现象概括为“自文本互文”和“他文本互文”,人物和情节的再现是指同一人物和情节在作家的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除了作家创作系统内部的互文性关系,梁鸿的作品还表现出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诗人艾略特提到:“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同的地方……”[1]阅读梁鸿的作品,可以看出她对鲁迅乡土文学的借鉴,以及对卡尔维诺等西方作家创作风格的有意模仿。第三章在叙事艺术方面,我们着重从梁鸿作品中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叙事风格三方面展开论述,对其文本内部结构进行学理研究。最后,我们从梁鸿创作中的特征和局限性两方面出发论述其独具魅力的创作理念及明显不足,其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于复调式的写作特征和多种文体融合的形式美;但是题材的自我重复以及对事件的先验判断成为梁鸿文学创作中的明显缺憾。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