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父”的根由:“无父”或“失父”
第一节 父亲的去世与“失父”的困苦
余华有不少小说均写到“父亲”这个角色不在场的情况,父亲的缺失使得子辈们的成长道路充满了艰辛。对于阮海阔、来发、李光头等人来说,“父亲”并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称呼,更是一种有着重要精神内涵的角色,在他们的成长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父亲的去世导致他们在子辈成长中的缺位,使得“李光头”们没有依傍,无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支撑自己,生存下去对他们而言成为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他们在困苦的挣扎中自力更生,恐惧与成长就在父亲角色的不在场中无所依傍地展开了。“失父”的他们既没有生存的能力,也没有生存的勇气。
在余华小说中,除了因为生老病死等客观因素而造成的父亲缺位之外,也有父亲因为生活生存的压力而选择抛妻弃子的情况。父亲的不在场与家庭的失衡让子辈不仅成为生活的弃儿,也可能成为“父权”社会中的弃儿。于是儿子们在巨大的失落与迷茫中走上充满焦虑的“寻父”的道路,在未知的路途中呼唤着“生理之父”、“血缘之父”的保护与庇佑。
一、父亲的去世与缺位
在长久的“父法”至上的社会历史、家庭伦理与血缘关系中,父亲这个角色有着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也关联着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多生存的重要因素,一旦失去父亲,或者说是失去“父亲”这个角色的保护与引领,子辈们也就失去了束缚与港湾,“失父”与“无父”的子女们就会在空前的自由中滑向精神的虚无,也会本能般地感到焦虑、不安与惶惑,南帆在《冲突的文学》中是这样描述子辈在“无父”状态时的情形的:“无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儿子得到了空前的自由与自主。用父亲名义传达的一切指令与戒律都取消了,儿子可以随心所欲,尊重生命所涌现的每一个愿望。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来,儿子又是处于悬空的飘游之中„„一切都显得无可无不可,遵从与反抗、规约与放任已经失去了区别。否定的力量推翻了父亲,瓦解了父子等级秩序,儿子再也不知道该肯定什么,为什么肯定。儿子的精神不再有给定的目标,它们不知所始,不知所终,不知所作所为。的确,除了及时满足短暂的快乐,‘伊特’本身提不出任何对待世界的长期原则。完全弃绝父亲——包括精神上的父亲„„虽然‘伊特’可能代表了最为原始的生命真实,但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不仅将毁灭他人,同时也将吞噬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之中,儿子如何管理自己?再进一步,他们又怎么可能接管世界,掌握世界,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①所以,失去了“父亲”的束缚和指导,也就意味着尚未成长起来的“儿子”们失去了家庭支柱的庇护,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和依赖的港湾,更失去了精神上的引领,从而产生了“失父”的迷茫和“无父”的恐慌。如何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或者说如何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和未来的方向,是“失父”与“无父”状态下子辈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他们“寻父”的根本动力。
................................
第二节 精神上的失父与“失父”的焦虑
这里所说的“精神上的失父”,指的是:父亲虽然在世但形同虚设,他们根本没有尽到作为一名父亲的基本职责,更有甚者还在算计和残害着子辈,子辈们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关爱,实际上处在一种精神上“失父”的境地。余华的很多小说都写到主人公的这种“精神上的失父”的境况,让读者看到:父亲高大、英雄的权威形象已不复存在,伦理的颠覆与道德的扭曲将“父亲”形象推上了审判席。父亲在儿子的成长中形同虚设的存在,使儿子们在困境中苦苦挣扎,迷茫、焦虑中的子辈努力寻找着心中的理想之父,渴望着获得精神的力量。
一、父亲虽在世但形同虚设
父亲对于子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子辈对于父亲的天然依赖心理,一方面可以说是孩子对于成年人的那种依恋,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在精神上需要被引领。在余华小说中,一些“父亲”尽管还在人世,对孩子却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他们要么无赖自私,要么对孩子不闻不问,更有甚者他们甚至亲手毁掉了孩子的人生。他们虽然在世但形同虚设,让子辈的成长缺乏正常的指引和指导,更是让他们在启蒙缺席的孤独成长之中焦灼与无望地自我挣扎,从而造成了子辈在精神上“失父”的悲剧。精神上的“失父”,意味着一种神圣秩序的沦丧,存在的荒谬与虚无在主人公“失父”的焦虑与惶惑中显现出来。
在余华的早期小说《竹女》中,“父亲”或许是因为生活的困难,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抛弃了五岁的竹女,独自远走他乡,十多年后父女重逢,只剩下一些依稀的、朦胧的回忆,相顾无言后,已然年老的父亲又在泪眼朦胧中蹒跚离去。父亲从竹女的生活中逃开了,未曾陪伴和指导女儿竹女的成长,竹女则生活在模糊的回忆与“失父”的伤感和焦虑中。
..............................
第二章 主人公的“寻父”及其意涵
第一节 寻找“血缘之父”的庇护
在余华笔下,无父的子辈们独自行走在人世。在湿漉漉的江南小镇、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在南门和孙荡、在飘着细雨的黑暗里,都徘徊着许多个孤独的“寻父”身影。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失父的孩子们脆弱而无助,他们努力寻找着“血缘之父”所象征的庇护,在绝望中呼唤着父亲、呼唤着温情、渴求一个确切的身份。血缘关系是人们由婚姻或者生育而产生的人际关系,它承载着家庭、家族等重要关系,因此血缘纽带中的父亲,对子辈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血缘之父”维系着原生的家庭,寻找“血缘之父”既是主人公在寻找身份的确认,也是在寻找父亲的庇护以及正常的家庭伦理,是在呼唤家庭伦理的重构、呼唤理想中的家庭亲情与结构的平衡。
一、绝望中呼喊的孤独少年
在绝望中呼喊的孤独少年,这样的形象在余华小说中其实有很多。比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鲁鲁、《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来发、《兄弟》中的宋钢等等,他们失去了父亲,也陷入失序的家庭中。秩序既是对人的一种规定,也维护了人的正常与安全,而失去父亲、失去正常家庭秩序的他们也就失去了身份确认、身体庇所和家庭港湾,所以他们呼喊和渴求着重构正常的家庭伦理。
寻找“血缘之父”,就是寻找父亲强有力的保护。《在细雨中呼喊》的鲁鲁,亲生父亲不知去向,于是跟着母亲颠沛流离,鲁鲁在被欺负得鼻青脸肿的时候总会威胁那些打他的同龄孩子:“小心我哥哥来揍你们”①,孙光林曾出手保护他,所以他乐意与曾被他称呼为“叔叔”的孙光林亲近,但又回避着对方对自己父亲的打听,他寻求想象中的哥哥的支持,实际上也就是变相地寻找血缘之父的庇护。《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来发是个傻子,他挑着担子送煤并以此谋生,别人总是喜欢问他父亲的去向,也因为父亲的去世,来发的名字都快被人们遗忘了,人们经常捉弄他、欺负他。他在绝望中回忆着父亲——父亲的话语、父亲的生病、甚至是父亲的责怪,追寻着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兄弟》中的宋钢,曾经拥有父亲宋凡平给予他的温暖父爱,但在他九岁那年,父亲死去,从此他失去了强大父亲的庇护,从前被父亲保护着的他不得不学捕鱼、插秧、割稻子、摘棉花等生存手段,还要被欺负,内心的绝望与凄楚不言而喻。
..............................
第二节 寻求“精神之父”的引领
余华小说中的“寻父”,除了寻找“血缘之父”的庇护之外,在另一个层面也是指无依无靠的子辈寻求“精神之父”——养父或继父的引领。对于那些父亲虽然在世但实际上形同虚设的子辈来说,他们有着不同程度上的焦虑,精神上“无父”的失落与苦痛让他们一直耿耿于怀,不仅是对于已知的生存苦难与存在困境的恐惧与疼痛,也是对于未知的将来的害怕与失去精神引领后的无根之痛,这是余华所说的一个人的疼痛,更是时代精神上的疼痛,精神上“无父”的缺失,是余华笔下的儿子的无奈,也普遍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无奈。
在养父、继父角色出现的背后,他们潜藏的心理渴求是呼唤重建时代精神,重建文化理想和他们失落已久的精神世界。在隔膜与疏远中,他们呼唤在失序的状态当中找到心灵上亲切的慰藉以及精神上有力的引领。
一、生父与养父或继父的对比反差
余华小说中常常出现生父与养父或继父的对比:生父是不称职的代表,养父、继父虽然与子辈们没有血缘上的联系,但是在精神上的关联却是不可割舍的。由此,也就会出现生父与养父、继父的在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对立与冲突,他们一方面无法割舍生父在血缘关系上那种与生俱来的牵连,另一方面又难以在精神失落的世界不把天平偏移向真正给予自己生活与精神保护的养父或继父。
生父在子辈成长中的缺席和不称职,让子辈在情感心理上对生身之父充满了疏远感和隔膜感。一乐寻何小勇、孙光林寻孙广才、杨飞寻亲的种种事实,都表明了他们寻找生理血缘之父的失败,于是他们开始寻求精神之父,养父、继父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正如《细雨与呼喊》里的孙光林一样,他 12 岁那年,养父王立强死了,所以他一个人不得不回到南门,但他内心觉得自己“仿佛又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有一些奇怪的错觉,似乎王立强和李秀英才是我的真正父母,而南门这个家对于我,只是一种施舍而已”①,养父王立强给予了他的生命中稀有的疼爱,因此他发自内心地感叹“比起孙广才来,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②。

文学论文参考
第三章 余华“寻父”书写的背景与独特性 .............................. 29
第一节 父子关系体验 ............................................. 29
一、成长记忆:作为儿子的余华 ................................ 30
二、成年以后的生活体验:作为父亲的余华 ...................... 32
结语 ...................... 43
第三章 余华“寻父”书写的背景与独特性
第一节 父子关系体验
余华的父子关系体验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作为儿子的余华在成长过程中所体味到的父子关系状况,二是作为父亲的余华在家庭生活过程中的父子关系体验,它们是余华“寻父”书写的重要经验基础。
余华对父亲与儿子的关系颇有深刻体会,在他看来,人生如同战场,父子之间免不了有交战,“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不过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②。这里,余华看到了父子关系中的碰撞与冲突,也看到了生命接力中父与子角色的戏剧性转换。在父子之战中,父亲对儿子的惩罚与儿子对权威的挑战似乎是持久的,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无师自通般学会怎样更加有效地去对付自己的父亲,让父亲一步步地认识到面对自己的儿子时根本就无可奈何,且“让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其实是短暂的,而失败才是持久的;儿子瓦解父亲惩罚的过程,其实也在瓦解着父亲的权威”③,余华的小说中的父子关系的书写,或多或少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父子关系的感悟认识。
余华的童年是完整的,但也不无缺憾。他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终日在医院的来苏水气味和手术台前来回忙碌,对幼小的余华疏于陪伴,加之余华的父亲并不善于言语上的表达,余华也并不理解父亲,父子关系趋于平淡。不过当余华长大以后,他对父亲有了新的看法,他看到了父亲的善良与伟大,尤其是当余华结婚有了孩子、自己成为了父亲以后,更是亲身体会到父亲角色的艰辛和父子之间的情感牵连。他对儿子的爱和儿子对他的亲情让他更多地去塑造温情的父亲。可以说,余华的父子关系体验,是余华“寻父”书写的重要背景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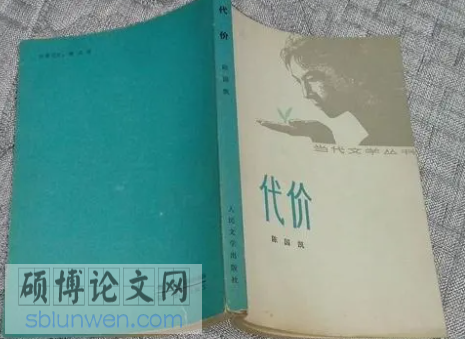
文学论文怎么写
.............................
结语
纵观余华八十年代至今的小说,“寻父”书写贯穿于其中,在“无父”与“失父”的描写中,又交织着“弑父”、“审父”等诸多现象。
考察余华小说中的“寻父”书写,会发现“寻父”总与对父子关系的描绘是离不开的,“无父”与“失父”的儿子们寻找血缘生理之父的庇护,也在渴望着精神之父的指引,并试图找到自我。而余华笔下的父子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余华创作转型后对父子关系的书写从父子对立走向了父子温情,但余华转型后的小说创作也表明,父子关系之间的隔膜与疏离并不是就此真正被谅解了,远离了现实中的暴力与欲望,也并不代表就此走入纯粹的生存与存在。余华后期创作中融洽和谐的父子关系书写,大多是通过描写继父、养父对子辈的关心与爱护来完成的。在余华转型后的父子关系书写中,孙光林与王立强,一乐与许三观,李光头与宋凡平,杨飞与杨金彪,这几对父子之间都有难得的温情式的“父慈子孝”,但恰巧又都不是血缘相连的亲生父子,由此可见,其“寻父”书写还有更多可供探寻的维度。而在“无父”与“失父”子辈的精神危机中,忍耐精神也并不能成为焦灼现实的溶解剂,慈爱的养父/继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父亲角色缺失的无根之痛,以及主人公对自我存在的根本性的怀疑。所以我们仍然能看到“寻父”背后的遗憾,这也说明子辈的“寻父”是未完成的。
在余华的“寻父”书写中,还有一些极具讽刺性的描写,比如山峰妻子的复仇也就是捐献山岗的尸体让他被四分五裂,于是山岗的睾丸被重植在一个年轻人身上,这位年轻人不久结婚并在十个月后有了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复仇反而阴差阳错地使山岗“后继有人”,而没有仇敌的李光头却自己主动选择结扎,所以从此以后不能为父,宋钢则是因生理缺陷与选择隆胸、阉割男性特征而不再为父,就是剔除和断绝了血缘上成为父亲的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情节还有:追求林红但求而不得的李光头做了结扎手术,居然有三十多个为了讹诈钱的女人宣称已经结扎而失去生育能力的李光头是她们的孩子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寻找血缘之父、寻找精神之父和寻找自我三个层面之外的另一种“寻父”,而走上行骗之路的宋钢在万念俱灰中卧轨自杀,冻结繁衍能力的李光头甚至把找寻精神归处的地方投向了远离浮躁现实的太空,这也意味着“寻父”之路的停滞与虚妄。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