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国的小城春秋
第一节 疼痛的记忆:忧伤的文学底色
一九七四年,张楚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程庄镇的周夏庄村,当他两周岁时,这座小城经历了一场七点八级的大地震,小城瞬间就被夷为了平地,二十四万余人在这场地震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地震发生时,张楚才两周岁,他的母亲费力地抱着他从窗户中跳了出来,他们这才保住了性命,就此躲过了一劫。张楚在《火车的掌纹》中以主人公(丁天的口吻)描述了地震发生时的场景,“那年我两周岁。我爸在北京当兵,我妈是村里的民兵连长。7 月 27 日晚上,因为第二天要开批斗大会,她认真地在写材料。凌晨 1 点时,她发觉房子疯狂地抖了起来——她抱着我跳出窗子。”[1]这场地震对张楚来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深深地埋藏在张楚的记忆深处,因此这场地震常常出现在张楚的小说中,例如《火车的掌纹》中的丁天,《U 形公路》中的阿三,他们都是因为这场地震而成为了孤儿。唐山大地震不仅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张楚个人来说,是重要的“人生事件”,并被他转化为文学中的重要事件。
张楚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小城里的普通人,他们为生计奔波,为生活操劳,裹挟着痛和泪在黑暗的生活中穿梭。生活的艰难将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紧紧包裹,就如同发生地震时的小城,灾难让人们无处可逃。每当张楚描写她们的生活时,就不自觉地将他们生活的小城与那场唐山大地震联系起来。童庆炳先生在《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认为:“特定的心境和情感是沟通现实经验与儿时记忆的桥梁。心境和情感愈跟儿时脑海的意象越吻合,所唤起的意象就越鲜明,心境和情感制约着意象的再现以及再现的程度。”
这场地震是张楚儿时最疼痛的记忆,这种痛感潜藏在张楚内心最深处,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张楚提起笔叙述小城人不幸的遭遇时,那种对小城人感同身受的痛感会让他不自觉地调动起埋藏在记忆深处的那场大地震,于是张楚就将这场地震和笔下的主人公联系了起来,这场地震也就成为了张楚小说主人公的一个悲惨遭遇。这场地震确实使不幸的小城人境遇更加悲惨,为平凡的北方小城增加了不平的经历,增加了小城神秘的面孔。但地震在张楚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只是简单地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提供了一个离奇的身世,张楚并没有将它作为小说环境描写的一部分和主人公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随着张楚写作技术的成熟,张楚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因而他在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将这场地震完全融到小城人的生命中,将它作为环境描写的一部分,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例如张楚重写的《刹那记》对这场地震的描写:“这很正常,一九七六年地震,整座城市死了二十四万人,据说当时天崩地裂鬼哭狼嚎。
.............................
第二节 发现小城:小城故事多
小城见证着张楚的成长足迹,在这里他从文艺青年变成小城中年,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具有烟火气息的人父,年少时张楚对小城枯燥生活的厌烦,到中年时身为人父对小城的接纳和重现发现,再到走出小城,对小城的回望与不舍,不同的经历、身份、心境让他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小城,让他在不同时间对小城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因而小城始终是他的文学根据地,他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孕育着属于自己的文学果实。
张楚大学毕业后回到小城,在税务局当起了一名公务员。小城生活的枯燥无聊,上班后同事的明争暗斗,再加上缺少志同道合的好友,这些使他对小城生活感到厌烦,正如他在随笔中写道:“在一个城市居住超过半载,便会开始坐卧不安,渴望着潜逃或分享的日子快些到来,在踏上火车眺望故居之地时,内心荡漾着憧憬与甜美的忧伤。”[3]纵观张楚早期的文学创作,我们会看到“逃离”的想法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学作品之中,从早期的《献给安达的吻》,到后来的《旅行》《我们去看李红旗吧》《冰碎片》等等。张楚逃离的不仅是小城,更是想逃离小城这种枯燥的生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因而“逃离”就成了张楚早期文学创作的主题。早期小说中逃离小城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比如《旅行》中爷爷奶奶的梦想就是走出小城,看看小城以外的风景,《冰碎片》中的静秋向往着大都市的生活执意离开小城。
小城虽小但仍会碰到同道中人,张楚上班不久后终于找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三五好友,他们常常在一家涮鱼坊聚会,边喝酒边聊文学,张楚曾在散文《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回忆到“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如果真有美好的时光的话。你一直以为只有你在摸黑走路,你孤单,你渴望身边有其他人的呼吸,然而当一根火柴擦亮后,你才发觉,原来你身边有很多和你一样默默夜行的人。”[1]不幸的是经历了时光的流逝,这群热爱文学的小伙伴也慢慢地走散了。其中一位怀揣文学梦的老大哥被生活糙磨成了只为生计而活的人,生意的冷清使他难以维持家里的温饱,儿子的病情使他日渐消瘦,文学的梦与情与他渐行渐远,张楚体会到了他内心的苦与痛,也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与无奈,他突然重新看见了小城人生活的不易与苦涩,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波澜壮阔,感受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情感喧嚣。
............................
第二章 小城的多重面孔
第一节 城乡之间:封闭又开放的小城
费孝通在“他的家乡话里,将集镇称为‘乡脚’,似比‘腿’更形象”[1],我们从名称中就可以看出乡村与城镇的密切联系,但如果仅从名称上来说明乡村与城镇关系,似乎有些片面,所以我们就要追溯到城镇诞生的源头以及从城镇人口的构成比例来论证城镇与乡村的密切关系。小城镇最初产生的目的是出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小面积的农家交换满足不了农家的需求,于是商业性质的交换场所就出现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乡村里的商业活动聚集起来的密集社区称之为“市”,即“在中国内地还通行着临时性的市集,各地方名称不同:街、墟、集、市——但都是指以生产者之间相互交互为基础的场合。”[1]随着商品贸易快速的发展,这些临时性的市集发展成为“永久性的社区”,费孝通将它称之为“镇”。所以自小城镇诞生起就和乡村在贸易方面就有着密切的来往。如今这种“市”几乎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城镇里的商场。从“市”到商场,这种贸易活动只是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它的贸易活动的实质却从未发生过变化。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城市与乡村》中也同样论述到“城镇”与乡村的关系,“多数城镇都是作为农业秩序本身一个方面发展起来的:在简单的层面上作为市场,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作为金融、行政管理和二次生产中心。”[2]从经济贸易层面来看,城镇诞生于乡村的母胎之中,城镇与乡村原始的交易关系从未改变,因而小城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乡村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镇高速的经济发展与便捷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再加上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耕地和播种面积的减少,乡村出现了大量富足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户籍制度的全面开放,再加上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这些因素驱使着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因而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小城涌入,费孝通将小城镇“看成农村人口的蓄水池[3],形象地说明了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这一现象。
乡村与小城的显性联系体现在经济贸易的密切往来与人口的流动与迁移上,而小城和乡村的隐性联系则在于二者共同的文化印记。如果我们从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乡村和小城镇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加以观照,易发现他们有一套共同的乡土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道德与伦理规训。从乡村迁徙到小城镇的流动人口自幼接受着乡土文化的规训,接受着中国传统的道德与伦理熏陶,即使他们搬迁到小城,骨子的伦理观念也难以改变;而小城里的老一辈人大多数也是从乡村搬迁过来的,他们的身上同样有着一套古老的伦理道德秩序。小城同乡村一样也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再加上小城稳定的生活秩序,他们奠定了小城传统的格局,所以无论是从乡村迁徙而来的外地人,还是小城本地人,他们都接受着传统伦理的熏陶,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依旧可以在小城人的身上看到传统文化的印记,但时代在发展,小城也在变化,当乡土文明遇上现代因素产生了奇异的化学反应,小城自然就成为文明交叉存在的异质空间,于是一幕幕的悲喜剧在这里上演。
...............................
第二节 灰色地带:罪恶又温情的小城
小城是张楚的成长基地,他与小城同经历,共成长,见证着小城发生的变化,小城自然也就成为他的文学根据地。他在这块土壤中完成了早期的自我认知和对世界的理解,此时的小城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是美好的,小城人在他心中也是可爱的;当他成年后,尤其是走出去后再回望小城时,此时的小城在他眼中变了模样,它不再像原来那么美好,甚至有些罪恶,而小城人虽善良,但也不乏愚昧和无知。即使小城有其罪恶的一面,但小城毕竟是张楚的故乡,他以温情的目光看向这座城和这里的人。正是因为张楚对小城过于熟悉,他才能以独特的个体叙事将小城的不同面孔呈现出来,美好与罪恶的小城面孔在他的笔下并不矛盾,相反这样的小城让我们感到如此真实。他的文学作品如同一面铜镜反射着小城在时代浪潮中的面影,见证着城与人发生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小城人的精神面貌是怎样随着小城的改变而变化。张楚在展现小城的时代变化上同时也执守着个人生命经验之上的独特表达,他在小城这片沃土上持续发力,书写着小城的喧嚣与荒诞,罪恶与温情。
小城是意外事件的频发地,因为它处于都市与乡村的交界处,在这片广泛的生存地带,西方文明与农耕文明在人们身上并存,而中西方文明又在这里发芽、变异,结果发酵成畸形的价值观,荒诞之事在这里上演也就不足为奇了,因而我们看到张楚笔下的小城是混乱的、荒诞的、颓败的。小城就其地理位置而言相对偏远,这里的人们放荡不羁,他们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缺少规矩的约束再加上官商勾结与政府的包庇,武力就成为了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这里成为了流俗之人与平庸之徒的聚居地,地痞流氓可以与游手好闲之徒随时在街市上演着肉与肉的交搏,暴发户与情妇之间的秘密不知哪天被撞破就引起一场腥风血雨之灾难,坐台小姐和寻欢作乐者演绎着快餐式的性交响曲,勒索、谋杀、绑架在这里频繁上演,肉体的交易也司空见惯。

小城即世界——论张楚的小城文学
第三章 小城折射大世界....................................... 30
第一节 现实追问:小城之变折射社会变迁.............................30
第二节 灵魂深处:小城人幽微的内心世界................................32
第三节 虚实融通:现实世界与精神空间.............................34
结 语..................................37
第三章 小城折射大世界
第一节 现实追问:小城之变折射社会变迁
小城作为乡村与都市的缓冲地带,是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交汇处,是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锋处,它体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进程,可以透过小城这个窗口看到时代的变迁以及中国社会独特的风貌。张楚笔下的小城是当下中国任何一座小城,他立足于当下,直面现实处境与具体语境,将小城故事放置到整个时代背景中,将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相结合,发现和看见了当今中国人的心灵幽处,回应了当代小城人的生存境况,反映了中国当代人的精神面貌,拓展了北方小城故事的景深与维度。
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而是体现在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等方方面面,这种变化对中国之前的格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瓦解,甚至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这种变化最为明显的体现在小城景观上,正如张楚在《我和我居住的县城——自述》中说:“慢慢地高楼越来越多,而且前年,县城终于出现了超过 20 层的高楼。这在以前是可不想象的,因为我们这里还经常地震,人们都怕住高楼;而现在,人们似乎什么都不怕了,不但不怕了,有了点钱还专门买好车。”[1]其次,我们从小城人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巨大的社会变化,从张楚在《中年妇女恋爱史》描写茉莉的两次婚礼,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巨大的变化。茉莉的第一次婚礼正处于 90 年代,茉莉的嫁妆就是当时流行的三大件,“红梅牌”电视,“新飞”牌冰箱,“夏利”的婚车;茉莉第二次结婚时,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初,人们生活水平和物质水平不断提升,私人轿车成了出行的流行工具,乘飞机旅行也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了。茉莉的第二次婚礼豪华得有些荒诞,黎江租了架小型直升飞机将茉莉从清河镇的娘家空运到洞房。正是通过婚礼的细节,张楚表明了时代的变化,他不去直接交代社会背景,仅通过个人的生活细节将个人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交织在一起。张楚的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记录了女主人公茉莉从少女变为妇女的人生历程,这部小说不仅是茉莉的人生缩影,还暗示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于个人史中可寻觅中国当代史的线索。颇有意味的是,张楚难掩想要“写史”的野心,全篇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中国每年的大事件,甚至宇宙各星球的大事件,将极小的个人与及广阔空间中的历史有意识地牵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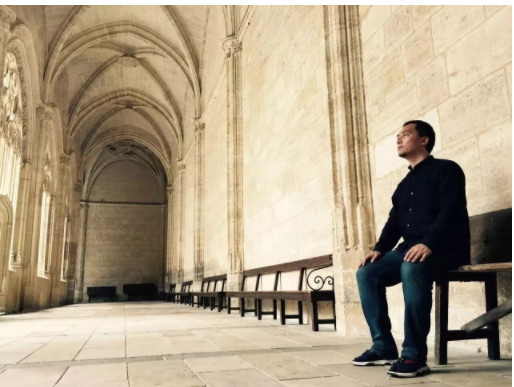
小城即世界——论张楚的小城文学
................................
结语
小城位于城乡的交界处,作为“城”与“乡”之间的缓冲地带,这里既能看到乡村文明的面影,又能感受到都市的浪潮,因而小城是一个矛盾结合体,是最能代表中国迈入现代化进程的地域。张楚笔下的小城可以是中国任何一座小城,它是当下中国最普通也是最有典型的县城,因为每一个小城在迈入现代化的路途中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向我们展示了飞速变化的小城,在这块腹地上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的顽疾和现代化的各种病症是如何交织进而影响着小城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找到了驱使小城人荒诞行为的内因。张楚呈现了在时间的维度下小城在现代进程中的变化,这就包括了小城内部一切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各种变化。张楚的小说是具有现实感的,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与历史信息,实现了文学对现实的介入,同时张楚又将现代主义手法融合到自己的小说当中,因此他的文学作品既有既有对时代、社会问题的回应与思索,又有诗意、空灵的抒情性表达,无疑他的小城文学对当代文学有一定的意义。
但张楚的文学创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纵观张楚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张楚小城文学的同质性,他在人物、故事与写作手法等方面多次重复,尤其是在解决小城人所面临的困境。他笔下的小城人大多是被世俗困扰的小城男女,他们虽然此时此地被困于小城,但是他们的内心都有着一种跳向远方的姿态——即对宇宙的向往,这种憧憬和向往使张楚小城人的内心世界不至于完全悲观、绝望,甚至还有一种精神期待,这种期待完成了他们的精神救赎,因而张楚为小城人摆脱眼前的困境找到了一条路径,即仰望宇宙。但小城人完成精神救赎的路径都是通向宇宙,这就到导致张楚文学创作经验性的雷同,好的作家应该自觉谋求变化,始终抵抗在题材、写法等方面的重复,在写作上有所突破。
而且张楚现在已经离开了他久居的小城,搬到天津在生活居住,那他接下来面临的创作问题就是,如何在大城市书写他的小城,如何将大城市的生活体验与小城的生活经历更好的结合在一起,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张楚曾在访谈录提到过他打算写一部长篇,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看整个中国的变迁,写出人的心灵史,当然张楚的中短篇小说也可以合力展现出中国的变化,但是对于中短篇小说创作张楚应该寻求突破,避免文学经验的雷同,这样才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我们期待张楚更优质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