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韩电影底层叙事空间意象与跨文化解读
第一节人格化的自然景观空间
自然景观空间可分为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两种类型,自然景观空间并非散漫随意的影像拼贴,或枯燥纯粹的意象堆砌,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都被充分赋予了底层人物的能动意识与真切情感,从而形成一种自然景观人格化的表述风格。
一、自然风景:对自然风物的亲近与融合
从古代诗词书画到现代影视,中国艺术创作者常常寄情于景、托物言志,借用忠实自然、纯净空灵的山水风光,表达对远离世俗喧闹繁华的向往与追求。因此,不论是处于乡土农村、城市郊外或小城镇边缘,自然风景往往比拟为人的善良品性,是质朴纯粹的底层平民形象的写照。
而韩国同中国相比较,尤其在对乡村风土人情的呈现上,相似的气候环境使得其乡村自然风景也具有传统东方蕴意的水墨质感,除此之外,更透露出底层平民贫困落后的生存状态。
同样,影片《暖》中,离乡多年的主人公林井河从城市归来与初恋情人暖再次相遇却己是物是人非的故事,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山村之间(图1.1.2)。对林井河而言,故乡的山山水水,不仅扮演了生活环境背景的角色,更是林井河业己逝去的初爱情感与无忧岁月的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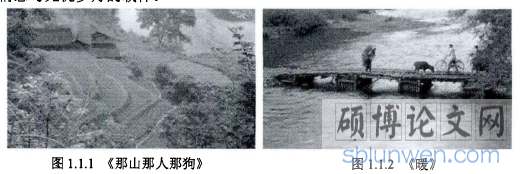
.......................
第二节生活流的家宅居住空间
家宅居住空间,主要由个体展开自我行动的个人独处空间,以及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与交流的家庭互动空间这两种空间形式构成,二者既是具体的生活居住环境,又是抽象的情感精神空间,在生活常态之中缓缓流动。
一个人独处空间:孤独个体的内心独白
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在社会的经济财富、文化资源、政治地位等各个层面,都处于边缘位置,他们是不受关注、漂泊无依靠的渺小个体,尤其是在个人独处时,这种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底层小人物的孤独生存境遇,在中韩两国电影底层叙事空间中,以个人独处空间的方式呈现,彰显了底层平民的内心世界。
如《那山那人那狗》对年迈眼盲、独守家中的五婆翘首期盼孙子来信的空间画面呈现(图1.2.1)。坐在自家门槛旁、面朝阳光的五婆身上是光亮的,但在她身后屋内是一片漆黑静默,两者形成鲜明对照,突显出了她内心的孤寂与凄凉。尽管两名乡邮员此刻站在五婆身边,于内心而言,她仍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同样,《外婆的家》中外婆家的门口,也是一个孤独个体的内心空间(图1.2.2)。外婆时常一人静默无言地坐在门槛上,遥望着远方的雾气山林。影片中的外婆尽管有女儿有外孙,但年岁已长仍独居乡村,生活贫困,但更加匮乏的是老人的精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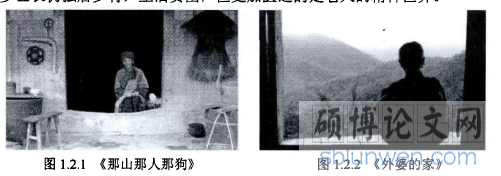
........................
第二章中韩电影底层叙事空间建构与写实化表达
第一节韵律化日常生活空间的选择与切换
中韩电影底层叙事空间的建构基础是日常生活,包含身居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物纷杂的社会关系及其从事的各项活动。基于此,影片多呈现日常状态的空间选择设置与生活细节的空间切换过渡。
一选择:日常片段的场所设置
底层普通人在漫长岁月中的某些闪光片段、令人悲伤或让人欣喜的生活点滴,被巧妙地置于日常生活空间之内,起承转合富有节奏张力与韵律美感。
如《外婆的家》中,导演有意设置了婆孙两人四次经过同一条山间小路的情景,物理空间范围虽然相同,但人物心理空间却是相异的(图2.1.1):

第一次,外孙初来乍到,对年迈又口哑的陌生外婆产生本能的抗拒,外婆走在前面,外孙远远地跟随,待外婆回过头,外孙便立刻停下脚步、转过身,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第二次,外孙独自一人去买电池,迷路被好心人送回,外婆特意绕到外孙身后,让外孙走在前面;第三次,等待外婆回来的外孙接过外婆的提袋,依然走在前面,并偷偷拿出了之前外婆买给他吃的巧克力派,塞进了外婆的提袋里;第四次,外孙贪玩跌进沟里受了伤,抹着泪一瘸一拐地向外婆走去,外婆拄着拐杖,加快了走向了外孙的步伐,擦干了他的眼泪。四次回外婆家的道路空间中,外孙对外婆的态度由抗拒到接受的转变,祖孙两人感情的层层递进得以展现。
........................
第二节个性化群像人物与底层空间的互动
影像中的人物无法在真空中生存,空间脱离人物便也失去了活力。中韩电影底层空间中,不论是乡村的农民,还是小城镇的工人,亦或是城市的小商贩等,都是个性鲜明而非脸谱化的群像人物。“每个人物的存在都具有感人的真实性。任何人都没有被归结为一种物态,或一种象征。”他们的形象构成了静态的底层空间造型,他们的行动构成了动态的底层空间造型。通过具有地域特色的口音话语与生命活力的肢体动作,底层人物群像得到了勾勒与还原,他们的个性特征也得到了鲜活展现。
一方言空间:还原真实市井生活语言
“语言本身是表达个人化风格、塑造个性化人物的重要方式,方言可以标示人物的个人身份和表达立场。”?而由于“方言总是跟地域联系在一起的,与某个特定的空间以及这个空间中人们物质形态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质朴的日常对话与俚语方言,往往具有类纪实性的特征,既再现了真实生活言语,描绘了乡情民俗,又虚构了独特的方言空间,显示出底层人物群像的生动有机的地域文化身份。
《三峡好人》中,来自山西汾阳的韩三明和来自太原的沈红讲着山西话,重庆奉节县的当地人操着四川口音,不同地域地区的人们处于不同的方言空间,这与他们在生活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和生存经验相关联,带着各自故乡的泥土或街道的亲切气息。不同于统一音调的普通话,影片中的方言空间尚没有遭受到公共话语的磨损,拥有更加丰富的表意和浓烈的感情色彩,塑造了淳朴善良的煤矿工人、拆迁民工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底层小人物形象。
......................
第三章中韩电影底层叙事空间隐喻与差异性探源..........31
第一节记忆空间与身体在地性........31
一记忆空间的呈现:意识空间的外化和剥离与身体空间的叛逆和驯服..........13
二记忆空间的实质:传统性的背离和回归与现代性的束缚和抗争..........33
第三章中韩电影底层叙事空间隐喻与差异性探源
第一节记忆空间与身体在地性
中韩电影中的底层人物,首先是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的,在对外部环境与自我位置的双重感触之下,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记忆空间,从而达成自我认知与内心成长的统一。
同样,《三峡好人》中,三峡库区内安土重迁的当地居民,则反映了农业社会思想的长久影响,以及底层平民对自身所处环境强烈的地缘认同感。《万箭穿心》中在丈夫死后一人挑起了养家糊口重担的李宝莉,《生活秀》中持家顾家并且做事坚持以来家的利益为准则的来双扬,分别穿行于汉正街和吉庆街这两个底层世俗空间之中,辛苦地劳作,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是仍是传统家庭观念,影片所塑造的两位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宝贵品质也都与仁爱、道义、孝悌、和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相呼应。
在韩国电影的底层叙事空间中,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是否应当回到传统,而是如何在时代巨变浪潮之中自立于世,而不至于被现代性所吞噬。
.....................
结语
中韩电影对底层的书写,遵循着东方电影强调空间感的美学传统,对身居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的生存经验进行挖掘,均从底层空间的物质还原层面上升到了底层空间的文化阐释层面,投射出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与思考,以及对社会与人性的沉重控诉和严肃批判,令人产生或平静朴实的感动、或震撼冲击的深思,形成了跨地域、跨文化的情感共鸣。
综上所述,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韩两国电影底层叙事空间,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不约而同地聚焦社会边缘、展现底层生态。现代城市与传统乡镇,既作为物理生活空间,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与地理特色,彰显各异影像风格;又作为社会伦理结构的意义空间,呈现出空间隐喻的复杂性与多义性。个人出于自我认知的需要,形成了个体的记忆空间;与他人关系的建立过程中产生了矛盾空间;与社会时代的悖逆或妥协则是现实空间的真切反映。个人、他人、社会三层关系交错互动,使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在底层叙事空间中得到完整呈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