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80后”女性写作梳理
第一节“80后”女性书写的创作语境
如前所述,考察“80后”女作家的写作背景和意义,既要注意她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全新环境,更要将她们放置于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二者的碰撞更添“80后”女性写作的独特性。
(一)“80后”女性写作具有独特的代际意义。
代沟形成的主要原因来源于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社会历史的迅猛发展会直接凸显代际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价值观的更新换代。价值观的差异是区分不同代际的核心原则,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80后”作家与前代作家有所差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80后”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包括道德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价值观越来越明显的代际分化、代际差异甚至代际冲突有着密切的关系,价值观的多元分化越来越明显地向社会代际关系领域展开,或者说,价值观的代际分代、代际差异和代际冲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重要表征之一。”他们直接从物质和精神文化上的贫困、闭塞状态跨入富裕和开放,价值观念的原始差异直接促成了“80后”作家在思维方式及文化立场上与前辈作家的裂解。九十年代后,社会继续着波澜壮阔的变迀,新技术、新思想层见叠出,可以说“80后”之前的作家仍拥有某些共同的群体性记忆,写作的心理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回应或有意识的疏离,本质上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信念感,但这在“80后”作家的认知范围中却非常罕见。此外,“80后”作为第一代完整意义的独生子女,她们度过了没有兄弟姐妹陪伴的独生童年,占据家庭的中心地位,更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独生的家庭结构在增添了孤独感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他们对待家庭、父母、婚姻、生育等方面的观念都有着更明显的自我化倾向。因此受到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及独生的家庭结构的极大影响,“80后”写作带有更多自由不羁、“唯我独大”的风格色彩。
其次大众传媒的丰富与发展,为“80后”写作提供了更为广阔开放的平台,这也是“低龄化写作”形成规模的必要物质基础。传统的大众传媒主要包括以书籍、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和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传播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传播,因此信息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互联网的进入和发展,彻底颠覆了传统大众传播的方式。我国于1995年开始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服务,互联网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迅猛的扩张开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大众传媒呈现出多元、开阔的格局,人们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更成为了信息的积极传播者,信息的来源也更加多样化。
.........................
第二节两种写作姿态及其特质
通过梳理“80后”女作家的资料可以看出,她们的创作有着较为明显的分期。自1998年《萌芽》杂志联合国内七所高校发起了“新概念作文大赛”,“80后”的作家们于新世纪初崭露头角,他们依托自身的校园经验创作了大量充满青春之伤痛、躁动或叛逆的文学作品。新世纪初至2005年的这段时期,“80后”女作家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岁左右,她们尚处于学生时期,作品主题多是对男女间感情、女性心理或性体验的青涩表现,抒发少女的小忧伤和小确幸,题材比较单一,内涵较为单薄,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在此后的几年里,逐渐走出青春期的女作家们开始步入社会,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她们有意识的将更多开阔的、厚重的东西掺入作品,例如张悦然的《誓鸟》对于宏大的史诗般意境的追寻,笛安的《南音》将汶川大地震、南方冻雨、福岛核事故等重大事变以及医患纠纷、工厂意外事故等现实矛盾通通杂糅进去,然而这些历史的、现实的因素在作品中仍然只是些无关痛痒的背景,与主人公性格的扭转或心理的成长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凸显性别意识的作品,女作家们面临着从“女孩”到“女人”的转变,愈加重视自己的性别身份,但在转变的过程中仍保留着青春的感受。
在2010年前后,文坛出现了诸多“80后”女作家的新面孔,她们自创作开始就于专业的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并刻意疏离了备受诟病的“80后”青春风格,加之本身也已经走过了青涩年华,她们自始便以成熟女性的身份书写女性的生存体验,女性主体意识更加明确,思考也更为深入。不可否认,她们仍然属于“80后”女性书写这一群体,代际差别作为一种“观念和文化取向上的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时代差异”,成人期与青春期的女作家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她们一定程度上拥有这一历史群体共同的两性观、爱情观等。然而,代际概念在将“80后”与前代作家形成区别的同时,也容易模糊一“代”作家内部的分化与差异,这些同代作家内部也会不断分化,年龄并非是将她们划分为两个群体的唯一标准,主要原因在于她们不同的知识结构及所持立场带来的不同的精神气质与心灵诉求,使她们在书写女性生活和命运时采用了不同的写作姿态。不同姿态代表了不同的身份特征,以及关照女性命运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本节将界定“80后”女性书写的青春姿态和成人姿态,它们呈现出了不同的写作风貌。
..........................
第二章两性关系之建构
第一节轻松反叛与超越
青春期的“80后”女作家成长于九十年代异彩纷呈的女性文化语境中,私人写作声名鹊起,在当时成为一处非常热火的文学景观。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不遗余力地向内延伸,带有深深的自我迷恋情结,通过对女性自己身体的认识而陷入对自我的深深思考,产生浓烈的依赖感和自恋情结,她们排斥现实存在,营造了一个孤寂的女性生存空间,在精神上孤芳自赏,牢牢地将自己封锁在个人的世界里,男性的场景和语境当然是被断然拒绝在外的。
尽管“80后”女作家已经基本走出了上一代女作家类似于“自恋癖”或“自闭症”的自我迷恋误区,但这些青春姿态下女性书写仍免不了继承了一些“自恋”的习气,对她们而言,女性与男性平等,或是超越男性都是轻而易举可以完成的。她们无意于贬抑或张扬男性或女性的性别立场,而是秉持着“轻松随意”的态度,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无意中让男性成为了成全女性自我体验和自我感受的配角,从而在两性关系的建构上也带有了强烈的女性的自我主观色彩。但不能说她们刻意制造了偏执的女性性别主义中心,因为“80后”女作家的一大贡献就是对男性形象的大方合理的呈现。
在春树早期的作品中,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对男性的贬抑色彩。《北京娃娃》中的B5、A26、李旗、赵平、G和T等等,我们只能看到这些男性人物的大致轮廓,名字也极易混淆,他们在春树的笔下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懦夫”,春树特别关注了男性身上无能卑琐的劣根性,与敢爱敢恨的林嘉芙相比,他们的懦弱无能、庸俗猥琐显露无疑。但是在大部分“80后”青春文学作品中,女作家往往都能正视男性形象,暴露他们的缺陷也欣赏他们富有魅力的一面,尤其在青春少女的眼中,他们往往会成为女性人物的爱慕对象或真心挚友。像是颜歌的《妖孽派秘笈》中被女主人公倾慕的男人,他是那样的美好,身材修长匀称,笑容温暖具有诱惑力,声音动听充满感情,只是说话就带有古朴的调子。张悦然在《水仙已乘鲤鱼去》中虽然设置了一个卑琐无能的生父,却也安排了温厚善良的继父来填补璟缺失的心灵。七堇年的《流景闲草》、徐璐的《永不凋零的春天》等作品,都塑造了一个个美好、清爽、温暖的男性形象。
..............................
第二节酷烈的自我救赎
对于孙频、马金莲这类代表成熟女性的女作家而言,她们清楚地认识到两性和谐的必要性,同时也深知追求两性和谐共生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容易。她们更多看到社会现状的苍凉与残酷,笔下的女性几乎完全褪去了自恋的气质,尽可能呈现出女性应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状态,以寻找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构建两性关系的新空间。
首先,是积极借助男性的力量。马金莲对碎媳妇、母亲或奶奶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致力于展现几近残酷的现实形态和生存真相,以及生活在残酷中心为身份而焦虑的女性。贫瘠苦难、闭塞落后的西海固,仍是一个典型的男权文化社会,即便西海固的许多男性因生计而远走他乡,或因缺乏责任感抛弃妻子,酗酒赌博破坏家庭,这里的女性也不可能像那些时代新女性一样彻底地漠视抑或蔑视男性,在马金莲的小说中,男性或者说男性的精神是始终在场的,如此一来,女性的生存处境就远比男性复杂得多,所要经受的困难也比男性繁复得多,对于这些被压制在传统强权文化下的女性来说,她们的主体身份建构更需要借助男性的力量。
在西海固女性的观念中,同男人一起劳作,努力赶上甚至超越男性,是女性应有的品质。对于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男性劳动力的家庭,女性更应责无旁贷地挑起大梁。《赛麦的院子》中,赛麦的父亲长期游荡在外无所事事、好吃懒做,弃妻儿老小于不顾,不能为家庭做出任何有价值的建设,而母亲却依然那么勤劳贤惠、任劳任怨,她一刻也不愿清闲下来,总是让自己处于忙碌中,干着男人的苦活重活,也干着女人的零零碎碎的活计,隐忍而顽强地支撑着一家的生计,她在白天和夜晚分别扮演着父亲、母亲两个角色,在丈夫无法指望的悲剧中,在整个村子对她生不出儿子的嘲弄中,坚忍顽强地强大了起来,在及其残忍酷烈的境遇里承担起男性和女性两份责任以支撑自己每个脆弱难熬的夜晚,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
...........................
第三章自我认同的确立.............28
第一节极端的臆想式表达............29
第二节尊严的重新定义.............32
第四章身体书写的探寻.............38
第一节青春实验..............38
第二节走向成熟............43
第四章身体书写的探寻
第一节青春实验
一如她们轻松随性的写作姿态,“80后”青春文学的女作家们对待身体也呈现出率性妄为的姿态,但是与爱情中主动选择了轻松、“属我”的态度有所不同,她们面对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往往表现出一种难以承担的无力感。不像90年代流露着旗帜鲜明的性别意识的身体写作,这些“80后”女作家笔下的“身体”是单薄的,女性身体上的文化“附加值”较前代作家大大减弱,其中的性别姿态也是比较暧昧不明的,未能让女性特殊的身体成为建构女性主体性的筹码。因此,早期的“80后”身体写作与其说是一场没有火药味的战争,不如说更像一次探索性的好奇而大胆的青春实验。这首先体现在她们模糊而稚嫩的性别意识上,青春期的女作家对于身体的书写不加修饰和渲染,无关乎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显与建构,只是率性而为的几笔带过,“轻飘飘”的身体并不能成为女性生命牢靠而坚实的根基,反而脆弱易碎,在身体的随性“飞翔”之后,有的只是她们无法掌控的自我放纵的失落感;其次表现为崇尚新奇、张扬个性,身体与情感常常处于分裂的状态,有时会给人混乱芜杂之感。
........................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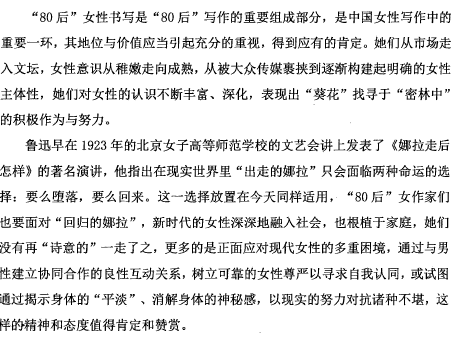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