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溯——石一枫小说创作背景及书写路径探析
(一) 石一枫小说创作背景
从诉诸于个体经验的“迷惘青春”书写到讲述多元世界里价值体系失范的“时代故事”,石一枫从无序的创作困境中走出,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自 2014 年发表《世间已无陈金芳》后,石一枫创作呈井喷态势,尽管近期作品多为中篇,但其思想内涵的深度确实与日俱增,这与他主动摒弃“复杂”回归传统的创作观念密不可分,也与他所处生活场域的熏陶有关。“回归传统”看似陈旧的创作观念背后是作家的深思熟虑。“科班”出身的石一枫,受过专业的文学写作训练且拥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阅读史使他能够甄别题材的优劣,独立思考自己要走的创作道路,从自身位移到多元世界,视野的开阔为石一枫打开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新世界,睿智的头脑及敏锐的眼光使作家能够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资本全球化、阶级壁垒、信仰迷途、道德沦陷等这一时代社会常见的问题于他的创作中显现;北京大院成长记忆的剥离使其从对“王朔”痞子式文学的喜爱转向回溯“新文学”的历史脉络,聚焦于身边眼前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精神成长和生命历程映射时代的变迁;把欣欣向荣的活力中国放置于全球化背景中,将人与时代、民族、世界勾连起来,为动态的社会勾勒出一幅浓淡相宜细节真实的现实写真图,体现出作家的责任与良知。
1.传统经验中的文化辐射
当代社会“媒介”的发达使作家创作过程不再显得神秘,消费语境下大众文化的兴起使肩负启蒙话语的精英文学被挤压退居边缘,随着 90 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众声喧哗的最后一次狂欢,“纯文学”几乎失去社会影响力成为聊以自慰的“圈子文化”。80 年代对市场及现代化最早敞开怀抱的启蒙知识分子在市场真正到来时“代言人”地位被冷落,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意识成为主导,快节奏生活及对物质生活的极端追求使“个人意识”膨胀,个体需求由参与和关注社会重大事件转向暂时的轻松和娱乐获取片刻悠闲。具有娱乐、游戏、通俗性质的大众文化自然而然获得拥护得以发展壮大。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王朔的异军突起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市场及大众的需求,“‘王朔现象’与 1987年中国商品经济的提出、国内‘市场化’的转型具备深度的契合关系,成为商品经济下的一种社会症候,成为 1990 年代覆盖性的市场文化的开幕式。某种程度上王朔也成为市民阶层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成为新一轮的‘文化英雄’。”①王朔作品的可读性、内涵的丰富性、新人形象的创造性、北京话大规模的使用和改造及对崇高的躲避与解构都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年,为他们打开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严肃叙事的幽默、颓废、日常的文本世界。共有的北京文化经验和生长空间使石一枫也深受影响且更能理解王朔叙事中所蕴含的深层内核。
..........................
(二)“为人生”的创作路径
从初期感伤忧郁的个人抒怀中出走的石一枫在近期创作中不断向现实靠拢,回归传统现实主义汲取力量,逐渐深化“为人生”的创作路径,这一创作观念是对“五四”以来的“为人生而艺术”创作观念的承袭与新变。“为人生”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实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收获之一,“1918 年 12 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大纛。”①这一“为人生”文学观念的提出与当时社会现实及文学环境密切相关,是对长期以来以注重娱乐、游戏人生的鸳蝴、黑幕小说的有力反击,也是对死板僵硬文以载道思想的批驳,是对现实人生的反映,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启蒙作用,无论是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疗救人生,冰心、王统照通过爱、美、善引导人生,还是许地山试图以宗教力量感化人生,都反映出文学对人生的启蒙作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长盛不衰也使为人生的创作观念葆有活力。不同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们的精英立场,石一枫始终以普通人自居关注当代社会巨变之下的暗影以及生存于其间的小人物们所面临的人生问题,既反映当代人形而下的生存难题也反映困惑几代人形而上的精神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坚定的现实立场讲述发生于这一时代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抱持理解而非同情和怜悯的心态关怀底层,书写沧海桑田中小人物们的命运史诗。正如刘大先所言:石一枫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改造,重启了一种启蒙叙事,但这种启蒙并非精英式自上而下的宣教,而来自于底层之间体贴共情、患难相恤以及在自省与行动中的自我启蒙②。
.........................
二、 在场——个体经验与青春书写
(一)成长道路上的荆棘与芬芳
石一枫从 2007 年发表科幻小说《b 小调旧时光》起创作呈井喷态势发展,先后发表可以称作“青春三部曲”的长篇《红旗下的果儿》、《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恋恋北京》以及“北京女孩成长史”的长篇《她和她妈的斗争史》和“亲情”主题的长篇《我妹》,这一阶段的创作显而易见是以作家个体经验为主,展示了石一枫对青年同代人青春逝去的缅怀和对其成长之路的思考,这条道路上既布满荆棘又芬芳无比,颇有“痛并快乐着”的意蕴。“作为一位标准的‘青春后遗症’患者,石一枫通过自己的写作,生动刻画出这个时代中各个患者在成长道路上的艰难挣扎及其负隅顽抗。”②成长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这条路上有如影随形的孤独,也有不期而遇的爱情,更有家人争吵之后温情脉脉的陪伴。石一枫的过人之处不在于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成长、关于爱情亦或是关于理想的故事,而在于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去讲,在油嘴滑舌的京片子语言泥浆中透出思想的光芒,并于讲述的同时去观察、思考一代人或一群人的精神出路及他们的价值取向,在走出校园、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在与他人的相互映照中逐渐走向成熟。他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去讲“自己”的故事,用严肃的态度去看待曾经年少轻狂、自恋、无所事事而又单纯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们,并用幽默的语言调侃逝去的光阴。因此,无论是关于成长还是关于家庭的叙述,都可看出石一枫小说创作的新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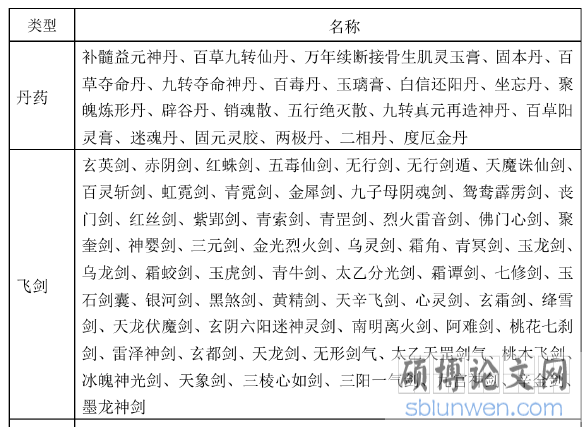
石一枫小说创作论
(二)温馨港湾的颠覆与重建
在传统乡土文明和儒家文化浸淫千年的国人的观念里,家庭、亲情和亲人是无可替代的,“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尔后有国之兴盛,家国是不分离的。然纵观百年现代文学史,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传承几千年的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反封建专制、礼教束缚的同时家庭之父被拉下神坛,“父”专制的一面被打破,“父”与子血缘至亲关系、人性本能的一面也被踩碎蹂躏,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在“反对父权的精神狂欢中”与血缘家庭相去甚远。新文学中家庭叙事伦理的崩溃以及破“旧”却没有及时立“新”的家庭秩序混乱的尴尬延续至今。因此,当代家庭叙事首先是从子(女)与父的关系入手,家庭伦理的重建是从子们寻父开始。如果说,新文学中家庭秩序的失范是由于子对父的背叛、挑战与决裂,那么,当代文学尤其是生于 70 年代以后的“子”们则是被他们曾觉醒了的“父”们所抛弃。“子”们面对仅作为“生理之父”的“父”实际上仍处在“无父”的窘境中。面对成长路上“无父”的状态,他们不约而同的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否定父的存在,嘲笑父辈们曾走过的路,进而否定家庭存在的意义,最终将自我封闭在狭小的自我世界里顾影自怜。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被迫走出自我小世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思想的成熟使他们学会了站在父辈的角度去探寻父辈走过的路,逐渐出现一批父辈的崇拜者,而更多的子则在理性回望基础上表示对父的理解并与之和解。79 年出生的石一枫大致延续了同代人关于家庭伦理的观念,又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进一步思考“家”之于当代人的意义,思考原生家庭对个人成长所起的作用及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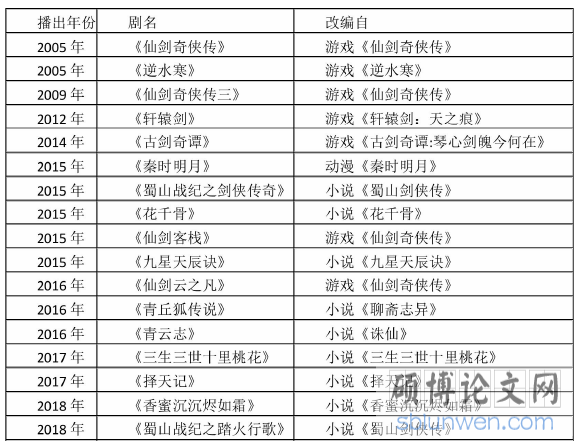
石一枫小说创作论
...........................
三、 介入——个体与世界的碰撞.................................. 41
(一)多元世界中价值体系的破碎与建构........................... 41
1.信仰缺失................................. 42
2.道德沦陷........................... 45
3.价值体系的文本建构................................ 47
结语............................... 69
三、 介入——个体与世界的碰撞
(一)多元世界中价值体系的破碎与建构
正如狄更斯所说:“那是个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①石一枫笔下主人公正是存在于这样一个难以以好坏界定而只能以“最”界定的时代,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前十年的二十年间。毋庸置疑,这是个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时代,也是个污水横流藏污纳垢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乏为公为民无私奉献一生的榜样,却也盛产一群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时代为伍顺潮流而动的人前一秒还在高声歌唱后一秒可能被潮流淹没失声痛哭,逆潮流而动的人只能抱守着不合时宜的信念被时代抛弃游离于社会边缘,霓虹闪烁照不见人心的黑暗,光与影的背后是不可测的深渊,人与人真正的成了他人的地狱。作家“石一枫通过自己的写作见证并呈现了致命的时代病——一个多元混乱的社会表象背后,赫然矗立的无坚不摧的冷酷无情商业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单向度一体化的价值系统对人赤裸裸的压迫。”②对于当今社会价值体系问题的思索,单一而绝对化的“成功标准”对人全方位的压迫,追逐金钱物欲而反被物所控制的人的“物化”,全球化境遇中阶级固化对底层人民的挤压,启蒙年代众声喧哗而导致的精神世界的多元混乱,外乡人进城却始终难以融入城市只能旁观甚或失掉自我狼狈逃窜的窘境,革命年代激烈的斗争精神在新时代继续发酵膨胀而导致的“新伤痕”,改革初期不合理制度尚未松动下个体顺潮而动却酿成的生命悲剧,石一枫面对庞大的时代慧眼识珠,发现不合理之下被损害、压抑、蹂躏最终被碾压成尘的小人物们的故事,以崇敬的态度、宽厚悲悯之心以及幽默而不失机锋的语言去书写、去观察这些小人物如何在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的年代苦苦挣扎,并尝试和他的主人公们共同求索更合理的价值体系。
.......................
结语
生于 70 年代末尾的作家石一枫,生长在文化底蕴深厚的首都北京,拥有地道的北京人性格:平和、自信、严肃而又带点“油”气,毕业于北京大学,任职于《当代》杂志,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使他在创作初期便彰显出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文风气质。“北京土著”的身份一方面为他提供了北京这一得天独厚的叙事场域,使他较于同代作家能够更敏捷的把握时代的变迁,一方面斑驳芜杂的信息流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也对其甄别事实真伪提出要求,值得肯定的是,“生长在北京的天然优势并没有让他耽溺于都市的繁华,他将目光投向城市的背后,在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之下,石一枫将他的目光投向更深、更远的地方。”①他的志向不在于此。从顽主们“青春后遗症”的青春泥浆里脱颖而出的石一枫,在完成第一次完好撕裂式成长的同时仍在酝酿下一次的破茧成蝶,这一点可以从其几部近作中有所察觉,由表现全球化背景下物欲对人的诱惑而走向失败的失败者故事《世间已无陈金芳》,到虽然孱弱但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伸张正义维护道德散发理想光辉的抗争者的故事《地球之眼》,石一枫向我们初步呈现出他观察与描摹现实的方式,表现巨变之下“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的尖锐矛盾。此后,《营救麦克黄》、《特别能战斗》、《心灵外史》进一步显示出作家观察及表现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不满足于鸡零狗碎的庸常生活的反复咀嚼,从时代入手,呈现动态社会的发展历程,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中将个体与时代、历史相勾连,将个体生命史诗纳入到当代社会发展史实之中。对于自身创作的转变,石一枫曾多次表明是由于“老同志们的耳提面命”,这固然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但作家的成长转变毋庸置疑源自于自我的反思、沉淀和磨砺,因此,其中的变与不变的创作逻辑链条便更加清晰。由此可见,石一枫的可贵之处不仅体现在其近期创作本身蕴含的深意及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更体现在其对自身创作观念地反拨和突围,回归现实传统,在旧瓶里装新酒,石一枫怀抱朴素的创作观念发现时代之新变,塑造系列典型形象从而为丰富当代文学人物谱系贡献一己之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