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北文学的再出发
第一节 作为话语背景的“八一五”光复“
不必想那过去的酸辛/也不必想那未来的快乐/如今我们战胜了仇敌/只管高唱着胜利之歌”[1],正如《东北文学》创刊号中《胜利之歌》的诗句所言,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东北的回归国土,“光复”成为了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较长时间内东北地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直至国共争夺战的再度打响,“光复”引发的热潮才随着“和平”“统一”等诸多梦景的消散而渐渐退去。时人谈论起“八一五”,是骄傲、憧憬,是激动、欣喜,种种情绪都被融入到以“光复”为背景的书写中。这是一段对国家、民族重拾乐观想象的时期,人们由伪满时只留躯壳的“僵尸”般的状态中回转,重新焕发出作为国民参与建设的热情。尽管在社会上存在有诸多的乱象,一些群体还在观望,但东北的文学界仍有先行者积极投身文学建设,或创办刊物,或发表社论及作品,为光复后东北文学的可能性作以探索。
第一节 作为话语背景的“八一五”光复“
不必想那过去的酸辛/也不必想那未来的快乐/如今我们战胜了仇敌/只管高唱着胜利之歌”[1],正如《东北文学》创刊号中《胜利之歌》的诗句所言,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东北的回归国土,“光复”成为了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较长时间内东北地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直至国共争夺战的再度打响,“光复”引发的热潮才随着“和平”“统一”等诸多梦景的消散而渐渐退去。时人谈论起“八一五”,是骄傲、憧憬,是激动、欣喜,种种情绪都被融入到以“光复”为背景的书写中。这是一段对国家、民族重拾乐观想象的时期,人们由伪满时只留躯壳的“僵尸”般的状态中回转,重新焕发出作为国民参与建设的热情。尽管在社会上存在有诸多的乱象,一些群体还在观望,但东北的文学界仍有先行者积极投身文学建设,或创办刊物,或发表社论及作品,为光复后东北文学的可能性作以探索。
一、由亡国奴向国民的身份转换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至 1945 年“八一五”光复,中国东北经历了十四年漫长的沦陷生涯。未能逃亡到关内的人们,只能留在东北过着亡国奴式的生活。在国家主权业已丧失的情况下,东北民众的生存生活需要与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随时处于如履薄冰的紧张状态。在东北日本殖民者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实际上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在其细密管制和不公调配下,日本人成为了一切资源的优先享用者,所谓的“五族协和”和“王道乐土”只是冠冕堂皇的幌子:从有权力耕种更肥沃的土地到筑建移民房屋,从掌握更先进的生产资料到独占一口干净的水井,在日本殖民者掠夺和倾轧下,中国东北的农民走向了破产和流离失所的绝路。随着日方战事吃紧,在每日必需的口粮上,日本人可以吃大米白面,中国人只能吃从前喂猪的“包米糊”和高粱,否则就会被认定是“犯私”的经济犯。这一点与日军占领北平后配发“共和面”是一致的,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便描写了专门发给中国人的“粮食”,这种像泥土一样难以下咽,散发着霉烂的臭味的“共和面”只会弄坏中国人的肠胃,在小说中祁老人的孙女小妞妞就因为吃不下这“怪面”最终饥饿而死。不仅是“经济犯”,日伪还制造了更多的“思想犯”“国事犯”,对东北的爱国青年、反满抗日人士进行大肆地抓捕和剿杀。作为亡国奴的东北民众,就这样以草芥般的地位挨过了十四年被殖民的生活,迎来了“光复”的曙光。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至 1945 年“八一五”光复,中国东北经历了十四年漫长的沦陷生涯。未能逃亡到关内的人们,只能留在东北过着亡国奴式的生活。在国家主权业已丧失的情况下,东北民众的生存生活需要与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随时处于如履薄冰的紧张状态。在东北日本殖民者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实际上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在其细密管制和不公调配下,日本人成为了一切资源的优先享用者,所谓的“五族协和”和“王道乐土”只是冠冕堂皇的幌子:从有权力耕种更肥沃的土地到筑建移民房屋,从掌握更先进的生产资料到独占一口干净的水井,在日本殖民者掠夺和倾轧下,中国东北的农民走向了破产和流离失所的绝路。随着日方战事吃紧,在每日必需的口粮上,日本人可以吃大米白面,中国人只能吃从前喂猪的“包米糊”和高粱,否则就会被认定是“犯私”的经济犯。这一点与日军占领北平后配发“共和面”是一致的,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便描写了专门发给中国人的“粮食”,这种像泥土一样难以下咽,散发着霉烂的臭味的“共和面”只会弄坏中国人的肠胃,在小说中祁老人的孙女小妞妞就因为吃不下这“怪面”最终饥饿而死。不仅是“经济犯”,日伪还制造了更多的“思想犯”“国事犯”,对东北的爱国青年、反满抗日人士进行大肆地抓捕和剿杀。作为亡国奴的东北民众,就这样以草芥般的地位挨过了十四年被殖民的生活,迎来了“光复”的曙光。
...........................
第二节 光复情境下的《新群》《东北文学》
《新群》与《东北文学》作为光复后较早创办的两份刊物,在微观层次上折射了这一时期东北文学杂志的大致面貌,同时也关涉到了其所处场域内引发人们关注的文学建设问题。一方面《新群》和《东北文学》代表着光复后东北文坛建设者的思想结晶,从发刊宗旨到建设蓝图,分别呈现出了各自的文学追求。另一方面光复后作家的文学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既是续接了前一段的创作里程,同时沦陷时期的创作也为这一时期的文学选择留下了伏笔。
一、文学建设的构想
第二节 光复情境下的《新群》《东北文学》
《新群》与《东北文学》作为光复后较早创办的两份刊物,在微观层次上折射了这一时期东北文学杂志的大致面貌,同时也关涉到了其所处场域内引发人们关注的文学建设问题。一方面《新群》和《东北文学》代表着光复后东北文坛建设者的思想结晶,从发刊宗旨到建设蓝图,分别呈现出了各自的文学追求。另一方面光复后作家的文学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既是续接了前一段的创作里程,同时沦陷时期的创作也为这一时期的文学选择留下了伏笔。
一、文学建设的构想
作为纯文学刊物的《东北文学》在发刊辞中表现出了对于东北文学建设的积极追求,是以“突破眼前的充斥于文学界的混沌状态”[1]、开拓东北文学的发展道路为旨归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正是出于改进文学现状的使命感,《东北文学》编辑者决心开展这项工作,并希冀以此融入到整个中国文学的建设中,刊登“真实”的作品、发表对创作有所裨益而不空泛的文学理论则成为了《东北文学》所追求的文学目标。《东北文学》在创刊伊始具有主观上的开放性,提出并不以任何文化团体的意志为中心,热切地期待真正爱好文学的“同路者”的加入和响应,
以期激起东北文学的创作热潮。前三期的《东北文学》封面上印有一只伸出的手,手心朝上五指张开,意在表达对共同建设的“援手”的渴望。
对于建设东北文学的具体方向,在《东北文学》的发刊过程中处于逐步摸索的阶段。热情与责任促使人们投入到文学事业中,但前进方向尚未取得共识,因此也没有提出相应的口号。《东北文学》认为文坛建设首先应做的是建立起文艺界的团结互助,减少由于敌对关系的互相攻击,以真挚的态度合力发展东北的文学事业。这一点初衷是高尚的,但在文坛分化的现实下实际难以实现。《东北文学》秉持的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文学态度,文学可以有多种样态,未来的东北文学应形成不以文学谋私利,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进行文学批评的大环境。《东北文学》第五期“论坛”一栏中发表有《惠然草》《寄东北作家》《东北文学改革论》三篇文章,汇集了有关东北文学建设意见的征文,也拓宽了对东北文学发展路径的思考。
................................
................................
第二章 回望伪满:“活是至尚,死是光荣”
第一节 日伪文化统制的罗网
《新群》《东北文学》的作家们走过了伪满时期的文化统制时代,迎来了光复后短暂的自由创作期,作为经历、见证了无数惊险时分和血色恐怖后的幸存者,回首曾经的纷纭往事,不免几多悲慨。在《新群》第三期“纪念季风”专栏中,提到了曾三度被捕入狱的作家李季风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活是至尚,死是光荣”[1]。从这八个字中也可以概括出沦陷时期东北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向,即活下去是作为人最根本的追求,对于作家而言,创作的不停歇也依赖着生命的继续。在日伪钢丝铁网般的文化审查制度的束缚下,作家们不得不费尽周折地进行着自我保护进而维系创作生涯。另一方面,在走向文学理想的道路上,作家们或隐或显地进行反抗和斗争、消解着日伪灌输的殖民思想,乃至以生命作为献礼,纵使自我随之消逝,也已完成了光荣的使命。
第一节 日伪文化统制的罗网
《新群》《东北文学》的作家们走过了伪满时期的文化统制时代,迎来了光复后短暂的自由创作期,作为经历、见证了无数惊险时分和血色恐怖后的幸存者,回首曾经的纷纭往事,不免几多悲慨。在《新群》第三期“纪念季风”专栏中,提到了曾三度被捕入狱的作家李季风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活是至尚,死是光荣”[1]。从这八个字中也可以概括出沦陷时期东北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向,即活下去是作为人最根本的追求,对于作家而言,创作的不停歇也依赖着生命的继续。在日伪钢丝铁网般的文化审查制度的束缚下,作家们不得不费尽周折地进行着自我保护进而维系创作生涯。另一方面,在走向文学理想的道路上,作家们或隐或显地进行反抗和斗争、消解着日伪灌输的殖民思想,乃至以生命作为献礼,纵使自我随之消逝,也已完成了光荣的使命。
一、作品的被审查、撕页、撤稿
伪满洲国在思想文化、舆论宣传领域设有文化统制机关弘报处,通过严格的审查制度来实现将“一切文化活动纳入殖民地‘国家’机器的控制和统辖之下”[2]的目的,进而巩固日本法西斯在东北的殖民专制。弘报处成立于 1937 年,至1940 年末扩大为思想文化统制的中枢机关,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一元化弘报体制。因此,日本殖民者在伪满洲国的文化领域织就了一张以弘报处为核心的密网,任何文字的公开发表都须经过弘报处的层层筛查,同时警察厅特务科与情报科等组织也为弘报处的文化审查延长了触角,并成为了弘报处逮捕和拷问各类思想犯、国事犯的机器。
伪满洲国在思想文化、舆论宣传领域设有文化统制机关弘报处,通过严格的审查制度来实现将“一切文化活动纳入殖民地‘国家’机器的控制和统辖之下”[2]的目的,进而巩固日本法西斯在东北的殖民专制。弘报处成立于 1937 年,至1940 年末扩大为思想文化统制的中枢机关,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一元化弘报体制。因此,日本殖民者在伪满洲国的文化领域织就了一张以弘报处为核心的密网,任何文字的公开发表都须经过弘报处的层层筛查,同时警察厅特务科与情报科等组织也为弘报处的文化审查延长了触角,并成为了弘报处逮捕和拷问各类思想犯、国事犯的机器。
弘报处的审查制度使得作品的创作空间变得狭小,只有符合伪满洲国文艺政策标准的作品才能获得发表的机会,尤其是在后期日本战争局势紧张、纸张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作品的出版变得愈发困难。在《东北文学》第三期发表了三篇文章:《关于<我的日记>的被扣押》[1]《<灵草>和我》[2]《这都是为了我的<七月>》[3],披露了作家们在伪满时期因未通过审查最终作品遭到扣押的经历。
............................
第二节 书写沦亡的悲歌
伪满洲国时期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作家不可磨灭的记忆,国家的沦陷与民众的苦痛激荡着作家的心灵,身为国民、作家的使命感驱使着他们不仅仅是关注自身所经历的险境与磨难,同时也以手中的笔叙写着沦亡时期的民间众生象。沦亡十四载的漫长生涯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家国的沦丧、悲悯的情怀交织成一股强烈的情感涌动在心中。与此同时抗战胜利、东北光复的景象并不能抹去笼罩在回忆中的的阴霾,《东北文学》与《新群》杂志的作品中呈现出的是对伪满旧影的再现与审视。
一、无路:民众的艰难挣扎
............................
第二节 书写沦亡的悲歌
伪满洲国时期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作家不可磨灭的记忆,国家的沦陷与民众的苦痛激荡着作家的心灵,身为国民、作家的使命感驱使着他们不仅仅是关注自身所经历的险境与磨难,同时也以手中的笔叙写着沦亡时期的民间众生象。沦亡十四载的漫长生涯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家国的沦丧、悲悯的情怀交织成一股强烈的情感涌动在心中。与此同时抗战胜利、东北光复的景象并不能抹去笼罩在回忆中的的阴霾,《东北文学》与《新群》杂志的作品中呈现出的是对伪满旧影的再现与审视。
一、无路:民众的艰难挣扎
在政治领域中“殖民”可解释为“在本国原有国土外的领土上,作移住的,放资的或根据的发展”[1],同时这种殖民扩张以人口迁移、资本掠夺和政治主权的掌控为主要形式,并将榨取来的所得内化为进一步扩大殖民地范围的推进力。日本在东北展开殖民统治以来,各年龄、阶层、职业的中国人都不得不在物质和精神上承受着日伪施加的无孔不入的压力,无论是生活的举步维艰还是生存的岌岌可危,人们终究面对的是无路可走的命运。惨淡的社会现实以一个个人物和家庭的悲剧结局呈现在《东北文学》和《新群》的作品中,社会的大背景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情境和素材,同时作家也通过这些作品刻画出一段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史,表现出了普通民众陷于囚笼中的恸哭,以及作者自身作为时局中人的苦闷。文学与现实的距离是存在的,但并不影响后来者在二者交织的纵深维度中无限地向这一时空中的精神领域靠近。
土地是农民赖以为生的全部身家,土生土长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后便失去了这份谋生的出路和指望,只能成为流民。陆望幽的小说《独轮车》中便描写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悲剧:一户祖祖辈辈靠耕地吃饭的庄稼人,在日本的殖民政策下被迫折物抵债,举家离开自己的田地和房屋,推着仅有的独轮车漫无方向地踏上逃荒的道路。自伪满洲国建立以来,农民面对的是更加惨淡的光景:无论粮食的收成好坏,日伪针对农民推行的无偿上交粮油的“出荷”制度是一年较一年催得紧;人人挨着冻饿,连低级的伙食包米糊也不能常常吃到,更不用说小米、土豆或是肉包子,都成了稀有的餐饭……
..........................
..........................
第一节 由《王荆山及其叭儿狗》一文引发的争端..........................33
一、 财主的“胜利”............................33
二、 敲诈的讹传与“无意义的文学”.........................35
第四章 战后东北文学的两条道路.................................46
第一节 左翼文学向工农兵文学的过渡.............................46
一、 鲁迅革命批判精神的继承.............................46
二、 文艺大众化的要求................................48
第四章 战后东北文学的两条道路
第一节 左翼文学向工农兵文学的过渡
东北文学在结束了沦陷时期的特殊发展阶段后,在光复后进行了对于东北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和尝试。一方面作家在走出伪满殖民阴影后一定程度上开始向原有的创作轨迹回归,并重新踏上自身所认同的文学道路;另一方面,东北文学的文学类型在这一阶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了向解放区文学转型的过渡状态。《新群》与《东北文学》恰恰体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文学发展的不同路径:一者是向工农兵文学的转向,另一者是五四文学脉络的承续。
一、鲁迅革命批判精神的继承
东北文学一方面在地域上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潮流保持着联系。20 世纪初东北文学在关内文学的影响下,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了左翼文学创作,壮大了左翼作家的队伍。但在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入东北后,东北左翼文学受到了殖民侵略势力的打压,东北创作环境在沦陷期间处于严密的审查和封锁中,以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东北籍作家不得不选择出走东北流亡关内,这些东北流亡作家在其后加入到关内的左翼文学阵营中,创作出了带有东北气息的抗日文学作品。留守东北沦陷区的左翼作家则在日伪的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着具有抗争意识的文学活动,在陈隄的回忆中,左翼作家们“继续了萧军、萧红、罗烽……等人出走后未竟的文学事业,以文学为武器和日伪统治者作了针锋相对的不妥协的斗争”[1]。也正因如此,在 1941 年接连发生的“12·30”事件与“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中,李季疯、关沫南、陈隄、王光逖等大批青年作家被捕,其组织的“左翼文艺青年读书会”也遭到破坏,东北的左翼文学由此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随着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伪文化统制消除后东北文学解冻,光复后的东北文坛保存并恢复了左翼文学的精神特质,由此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左翼色彩的文章。
...........................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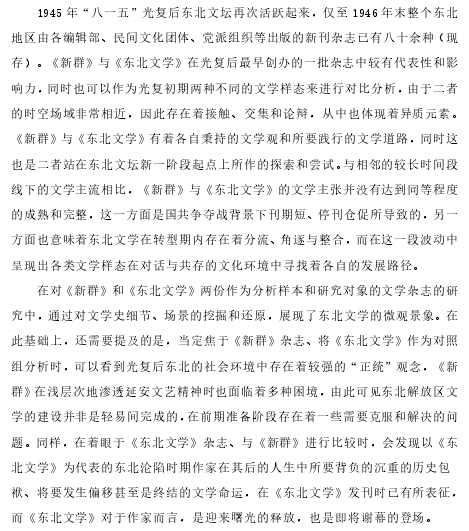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