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动物叙事中的西部精神熔铸
第一节 鉴照人性的纯真品格
自西部现代文学发轫以来,作家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这既是对百年新文学书写传统的接续,也寄寓着他们对现实人性的美好期冀。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西部作家借助动物构筑了独特的西部动物叙事小说,试图用动物这把钥匙,探析西部大地的奥秘,同时通过对动物纯真生命状态的观照,发现某些动物与人共有的美好品质,意识到人性发展的应然路向,力图通过自己的创作匡谬正俗,祛除人性中恶浊的东西。很多西部作家正因愤嫉于现代人性的诡谲,所以将目光回放到一些处于原始自然状态的西部生灵身上,由此,他们发现了西部动物所特有的纯真品格,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便由衷赞美,并自然而然地将动物的纯真与现代人的异化进行对比,以致其创作不仅揭示出了动物的某些精神价值,同时也具有了现实担当的意义。
首先,一部分西部作家注视到同样是遭逢极限境遇,动物与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这一点,专注于叙写动乱年代的发生在动物与人身上的离奇故事。在叙述的过程中他们为我们揭示出:人处于极度匮乏或压抑的状态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人性幽暗、恶浊的一面,会有某些令人不齿的非常行为产生,而动物在面临相同情况时,却常常能守住生命的本真,一如既往地善良、忠诚、纯真。两相对比,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在一些简单甚至“低等”的生灵面前,就显得极其不堪。这样的创作并不会人为建构出一些动物本来没有的品质,作家大都是“实话实说”,让读者意识到动物品质的美好,并对“人性”这一概念产生深入而持久的反思,避免生命中可能出现的异化,避免对人性之恶视而不见。李本深在小说《汗血马哟,我的汗血马》中讲述了一匹绰号为“感冒”的汗血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我”与“感冒”都是刚入军营的新兵,免不了受老兵的欺负,在一次骑行过程中,老兵们策马来冲撞我,“感冒”则在“撞击中竭力保持平衡,在这力的对抗中竟如一堵岩壁似的沉着、坚韧”,2最后老兵自己被撞落下马。“感冒”也曾为了保护“我”与一只狼恶战,忍着伤痛将狼踢出一丈多远。然而在“文革”的狂潮中,“感冒”被抛出了革命队伍,它那惊心动魄的“英雄气概”逐渐丧失殆尽,精神甚至因此奔溃。原本可以自由驰骋在草原的汗血马,被送去豆腐坊拉磨,“它很快地见老了,瘦骨嶙峋、歪歪斜斜,浑身毛色发暗……最终竟变得空壳似的麻木了。”
.............................
第二节 刚烈不屈的血性精神
早在现代文学时期,鲁迅就关注到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他从人类学的角度探析了中国人“人与兽”的纠葛,他一方面肯定人的人性,否定人的兽性,另一方面又深感人在文明进化中所失落的一些不该失落的天性,呼唤从动物那找寻中国人匮乏的精神气质。在他看来,狮虎鹰隼等动物身上的自然野性才是最“伟美的壮观”3,并发出如果“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4的喟叹。沈从文亦发掘湘西边陲雄强的原始生命活力来作为民族生命的根柢,在他看来那些山中勇猛的虎豹,“即或只剩下一牙一爪,也可见出这种山中猛兽的特有精力和雄强气魄”,5这才正是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应丢弃的气魄。西部作家亦渴望借助动物的生命强力彰显西部边地血性雄风,实现对民族精神的血性重塑。
自唐代边塞诗始,崇仰风骨、寻觅刚健的壮志豪情就已经熔铸进西部文学的血脉,这既体现了古代诗人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之下生发出的守土戍边、保家卫国的冲动,也体现出他们置身西部辽阔大地和酷烈环境中感受到的最为深切的心灵激荡。一首首慷慨激昂的边塞诗句不断激励着戍边的将士和耿介的文人,释放出一个伟大时代的最强音。19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放纵欲望、崇尚消费、耽于游戏,当代“文明人”逐渐在资本建构的怪圈里变得“苍白、干瘪、乏味、困窘、卑琐、怯弱”6,精神的乏力与生命的委顿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弊病。西部作家焦虑于现代人精神的委顿和迷茫,决心唤醒西部文学血脉中的刚健力量,以期重振人心。西部作家长久在西部大地上生存,在对西部动物的瞩目中,发现了其身上所具有的血性精神,即一种以顽强的身姿去对抗命运,刚直不阿、不惧生死,勇于拼搏的精神,他们致力于将西部动物的这一精神发掘出来,一方面在写作中以动物精神来扩充西部精神,另一方面表明了其对社会现实的担当意识,力图发扬这种精神来重塑现代人日益萎靡的精神和失血的人格,构筑起西部精神高地以救赎人的精神困境。
................................
第二章 动物叙事中的民间信仰根植
第一节 重返万物有灵现场
从远古华夏大地上的各部族视各种动物为其图腾,寄予敬畏和崇拜,到先秦两汉《诗经》《山海经》《庄子》中“寓言”“神话”的动物描写;从晋唐宋搜奇志怪小说中的光怪陆离的“动物化形”与“动物报恩”,到元明清小说中兼具人生批判的动物书写,再到现代文学中变化多姿、异彩纷呈的动物叙事主题与模式的显现,动物叙事这一写作类型在不断的传承与衍生,至今已呈现出“一种相对完备的叙述态势。”1然而在这其中却有一种恒定的“情感基质”2未曾发生变化,即“万物有灵”和“动物崇拜”,其中积淀着中华民族对于动物的一种朴素认知和情感因子。简单来说,“万物有灵”是人类在原始文明时期普遍具有的一种对于世界的认知,指的是认为世间的各种自然物都像人一样有灵魂、有灵性,相互之间可以凭某种超自然的方式沟通、影响彼此的信仰或信念。这样的认知之所以会产生,与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生产力低下,对抗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而对于诸多自然现象发生其背后所遵循的规律又认知不足,所以按照一种神秘化的想象的方式去理解自然万物、生命存在有关。“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1是该种认知的普遍预设,在人与自然缔结的“生命社会”中,“人与动物、植物都处于同一层次上。”2最终形成了对动物的敬畏和神性的向往的情结,也积淀成从古至今不断传承的情感基质。
在西部动物叙事小说中,自然少不了这种情感基质的沉淀,这种延续千年的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在西部多元民族文化的映照下更加光彩夺目,一场原始与现代的碰撞、心灵与心灵的回响,在西部大地上演绎出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动人篇章。对西部作家而言,他们在小说中试图复归一种古朴的自然环境,其中生存的人们是信奉“万物有灵”论的。在这背后体现出的并不是作家想要回到一种原始,物我不分的不自知的状态,而是作家深知这种一种万物有灵观念背后所传递出的人与自然生命的情感连接,这种情感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愈发断裂,而这种断裂势必会给人类带来不利,因而,他们借助重返现场,向着原始民间信仰的复归,实现对当下人精神困境的反思。
............................
第二节 人与自然的龃龉图景
西部作家在动物叙事中表现民间信仰、重返万物有灵、人与动物平等和谐共存的现场,目的不是简单的怀旧复古,而是要在其文本中寄予对当下生态恶化的忧虑与反思。西部作家对于现代生态景观有所观照,对于人与自然无法和谐相处感到焦虑并作出反思。与西部作家构筑的人与动物诗意栖居的美好图景相比照,在另一些文本中,他们则致力于揭示出动物遭遇的悲剧,以此来说明人与自然的龃龉,这已是当下人们不得不直面的社会现实。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膨胀与人的理性的异化,人们越发痴迷于自身的能动性,人们开始“推倒供奉着动植物的神庙”,1动物随之成为人们的盘中餐、口中食。早先处于人类“伙伴”位置的动物便成为人类野心与利益不断膨胀的牺牲品,“人类大屠杀”的阴影还没有消散,一场“动物大屠杀”早已袭来,并逐渐演变为具有现代意味的“新的风险景象”,2随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这场屠杀中遭到瓦解,人类彻底陷入到自我中心主义的怪圈之中,也早已失却了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
自杨志军 1985 年发表小说《环湖崩溃》始,对西部的生态忧思就成为西部作家难以割舍的情感,面对西部大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被破坏、野生动物被捕杀的惨痛现实,以及世纪末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生态思潮及生态文学创作潮流,西部作家从西部的现实处境出,首先揭示出人与自然的龃龉图景。在这一图景中,人类过度地向自然索取,最终在自然的失衡中招致了自然的报复。在杨志军的小说《环湖奔溃》中,对于青海湖生态的破坏是从对一只瞎熊的碾压开始的。“我”跟随父亲的拓荒队进入环湖的草原,我们在与一只熊的邂逅中用汽车轧死了它,瞎熊的肚子“被碾成了肉酱,身下是流淌的兽血……”1也许是为了心中的内疚,“我们”将瞎熊的孩子领养,并取名“库库诺尔”。在经历了数次的开垦后,荒原早已不成面目,在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库库诺尔一掌击死了父亲,更击碎了人们对于开拓荒原自以为是的狂傲。如果说库库诺尔向父亲的复仇表明了自然的一种因果报应,那么随之而来的毛虫潮更是将人类的罪恶无限放大,人类利用技术和动物的本能,为其精心构筑了一个以爱之名的陷阱,欺骗它们并将其残忍杀戮。对杨志军而言,他将文字的触角伸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处,在以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在书写着人与自然惊心动魄的断裂,他以对自然的无上敬畏,试图唤起人们对于自然的忏悔与敬畏。杜光辉则借由“藏羚羊”开启了他对人类的“拷问”。在杜光辉的中篇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美丽的藏羚羊“喀秋沙”惨遭人们的毒手,死在了猎枪之下,“子弹穿透了‘喀秋莎’的肚子”,2鲜血瞬间染红了雪地。“‘喀秋莎’痛苦地抽动四肢”,3眼里只剩无尽的绝望。人类凭借对于自然的狂妄,一步步逼近自然,向自然索取并毁灭自然,最终导致生态失衡与自然的满目疮痍。在小说《可可西里的格桑美朵》中,黑心的人们则残忍地砍掉藏羚羊的头,剥下它的皮运往国外贩卖。无数生灵的皮毛都昭示着人类永无止境的贪婪欲望。人类凭借不断扩张的野心、不断发展的技术,向自然无限度索取,自以为能使自己的生活不断变得更舒适、更优越,实际却可能造成生态失衡,进而对人类命运带来灾难性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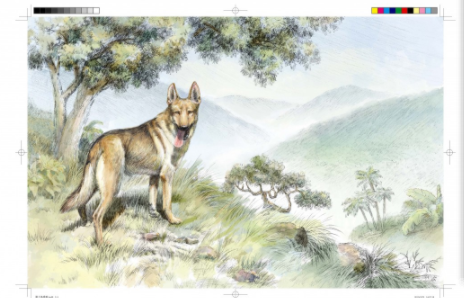
新时期以来的西部小说动物叙事研究
第三章 动物叙事中的生命存在之思...................32
第一节 生命之子的存在体认...........................................32
第二节 死亡、救赎与永续的赞歌................................35
第三节 文学与生命的相融共振......................................39
第四章 动物叙事中的现代性反思................................43
第一节 动物在乡的牧歌追忆.........................................43
第二节 动物进城的悲剧叹惋.........................................48
第三节 无所归依的文化反思........................................52
结语..................................55
第四章 动物叙事中的现代性反思
第一节 动物在乡的牧歌追忆
人类的文学创造中一直蕴含有一种牧歌情结,它指的是对原始古朴、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景象的向往,反映了人亲附于自然和大地的本能需求。在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对家乡、原乡的眷恋和追慕,对田园牧歌的欣羡和描摹一直是其重要的审美意蕴和书写主题。这是因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很难不对乡土故园保持一种深情的凝望,敏于美感和诗意的作家诗人很难不把其感知的触角伸向旖旎的田园风光。新时期以来,很多西部作家切身感受到了乡土田园因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冲击,诗意逐渐残缺、美好逐渐不在,心中泛起悲感浓重的怀旧思乡之情,他们意欲以自己的笔触,为迷人的牧歌景象绘一幅岁月的遗照,唱一首深情的挽歌。在这其中,西部作家亦叙写到一些动物生存活动于乡间的故事,注重交代在一种充满前现代意味的环境中,人是怎样与动物和谐共生、和睦相处的。通过这样的描绘,西部动物的灵性与西部乡土的迷人便跃然纸上,读者便能被人畜共居的前现代世界所打动,进而思索对动物与人的应然生存状态。可以说,西部作家创作此类小说是为了重现人类集体记忆中渐趋模糊的乡土文明,抵制现代城市文明过度发展带来的弊痼,这样的书写有其独到的魅力和价值。
对西部作家而言,他们笔下的动物书写营构出的是一种西部乡土诗意景观。在西部作家的小说的文本中,动物、植物与人共同组成一个和谐自足、诗意盎然的前现代世界。在红柯的笔下,草原是如画般的迷人:“天空升起绿色的光芒,草原出现在地平线上,马打出一串欢畅的吐噜……草地上的牛群,它们都是出奶很多的花牛,黑白相间,跟拼贴画一样。”1在王新军的笔下羊群与青草相映成趣:“坡上的青草一直向下铺,一直向下铺。它们像水一样从高处卷下来,漫过了所有平缓的山峦和低矮的树木。羊群如同漂浮在绿色草面上吉祥的云朵……”2在龙仁青那里,阳光、青烟、帐篷、牛羊共同组成了温煦的草原画卷:“斜斜的阳光细柔地盖在草原上,浓密的邦棉菜微微闪耀着一片白光。和吉明家的帐篷同属一个圈窝子的几顶帐篷平和地吐着一缕袅袅地青烟。帐篷的四周,已经放出羊圈的羊群和已经解开栓绳的牦牛悠闲自得地啃吃着青草。牛羊的叫声使平静孤独了一夜的草原显得活跃而有生气。”3由此,可以看出西部作家是将动物作为其构筑西部地域景观的诗化呈现,进而将人与动物的紧密联系交织成诗意的言说,以一种对田园牧歌的追忆来确证自己的乡土情结,最终将小说的精神通向一个理想、和谐的境界,传递出作家们对“前现代”乡土世界中人畜共存、自然本真的生存样态的依恋与怀想,进而在“乡土——诗意”中寻求心灵的安放之所。

新时期以来的西部小说动物叙事研究
..............................
结语
“动物叙事”作为一种叙事类型,其所具有的精神品质、伦理指向与情感内蕴是逐步构筑起来的。中国的动物叙事创作和对它的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研究者的论述不够深入,大都是从题材、书写角度等方面开掘此类作品的价值。实际上优秀的动物叙事并不仅仅是“写动物”那么简单,并不只是能满足我们对于边地景象、异域风情的好奇和对于原始生命力的向往,这些小说往往意蕴丰赡,既能给我们提供精彩的故事情节,亦能给我们以思想的启发、心灵的感动。西部作家笔下的动物叙事通常更容易含纳丰厚的精神文化意蕴,这是因为西部野性生灵众多,且其生存环境受到现代人类文明的影响较少,发生在动物身上的精彩故事或有关动物的瑰奇传说自然数不胜数,而西部作家又通常对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城市景观怀有一种警惕乃至拒斥的心理,偏爱于自然淳朴的前现代景观,遂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发现去摹写动物们的事迹。本文的着力点正在于通过文本细读,发现西部动物叙事最主要的精神文化蕴涵,将其揭示出来的同时也力图探析这些蕴含何以形成,有什么样的价值。
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新时期以来的西部小说中的动物叙事。首先,笔者通过大量细读和审思,发现这些动物叙事中的动物往往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精神品质,即不因生存境遇的改变而变更的善良、单纯的“纯真品质”,不畏强敌的压迫和挑衅、勇于反抗和拼搏的、至死也不屈服的“血性精神”,以及面对艰苦且恶劣的自然环境,绝不放弃生活的信心、坚持砥砺前行的“韧性力量”。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动物叙事中的动物之所以常体现出这些精神品质,一方面是因这些精神乃是西部作家心中所崇仰、所欲拥有的,另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西部大地的荒旷、粗粝、贫瘠培育出了西部动物的这些品质,也就是说这些精神品质具有“西部性”的特征。笔者得出结论,西部动物叙事中,动物身上的这些美好可贵的精神品质,绝不只存在于小说中动物形象的身上,同时也存在于西部人的心中,体现于现实中西部的人和动物的一举一动,所以这些精神可以被看作是西部精神的代表;西部动物小说以此将西部精神很好地熔铸进了文本。其次,笔者发现西部动物小说的情节中常常显现出一种“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也即西部作家笔下的动物故事,常将一种“任何动物都具有灵性、神性,人对动物应保持敬畏”的理念传递给读者。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