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铁生忆旧主题小说的“自叙”特征
第一节 “真”的表现:取材的私人性
自叙传小说家们将“自我”视为折射世界的特殊个体,他们重视从外在世界获取的私人感受,史铁生早期的小说创作中也呈现出这一特点,他没有宏大叙事的意图,坚持写“真人真事”和生活里的小事,文本之中处处体现着他所强调的真诚。小说总是跟随着“我”的自叙节奏慢慢展开,所有描写画面都带着“我”的情绪色彩。这些小说也可以看作史铁生的生命备忘录,他一一回忆,一一记录,是为了使生之印记不被轻易地抹去。
一、回顾知青岁月
在史铁生的人生旅途中,最让他难以忘怀的,应该就是那一段插队岁月,他曾写了无数的作品来怀念,《黄土地情歌》、《相逢何必曾相识》、《插队的故事》……当时的史铁生意气风发,还不识命运的真相,怀揣着一腔理想与热情,踏入了那方此后一直魂牵梦萦的土地,也由此铺叙了日后令他名声大噪的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相比同时期以张承志、梁晓声等为代表的知青文学,《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可谓别具一格,它不是英雄主义的礼赞,也没有历史批判和政治讽喻,只是一曲平淡悠远的青春牧歌,为知青文学提供了另一种叙事可能。当然,这一场史无前例的的上山下乡运动,无疑给当时所有的青年人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史铁生也不可能例外,假如没有这一场运动,没有高密度的劳作,或者只要有好一点的医疗环境,他的下半辈子就不用与轮椅为伴,他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怨恨,可是他没有。我想,其中永远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在这片黄土地上,留下的是他最美好的青春。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可以看作是史铁生纪实类小说的代表,它向读者展示了史铁生真实的插队生活,以及当地特殊的风土人情。清平湾真实的名字叫做关家庄,是陕西延川县的一个小山村,在小说中,作者将这块地域化名为“清平湾”。这里的清平湾,不仅是史铁生插队的关家庄,还是所有下乡青年梦里遥远的故乡。《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确符合自叙传小说的典型特征,他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以自身原型为素材,记录自己插队时的真实事件,以至于常常有读者直接将文中的主人公与史铁生本人等同起来。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在清平湾插队的知识青年,插队期间患上了腰腿疼的毛病,队里为了照顾“我”,就给“我”安排了喂牛这样一份相对轻松却也十分重要的差事。此后“我”一直和村里的白老汉一起喂牛,直到病情恶化回到北京。后来“我”坐上了轮椅,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白老汉,想念喂过的牛群,想念回不去的清平湾。熟悉史铁生的读者都不难看出,这简直就是史铁生真实经历的复刻,这里的叙述者与作者虽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是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主人公的经历之间却形成了相互指涉的关系,引领着读者主动去探求主人公背后的作者的所思所想,这实际上完成了“我”的统一。
...............................
第二节“真”的表达:结构和叙述的主观性
自叙传小说,虽名为“叙”,实则为了抒情。这一体式自五四发端以来,虽经过长时间的变迁,纯粹意义上的自叙传小说已经消失,但是它却融入了后续的文学创作之中,继续发挥着它的潜在影响,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也可以看作是自叙传小说的一种变形。就史铁生而言,自叙传小说的抒情功能为他抒发心境体验,表现个人情愫提供了便利,不同于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取材于广阔的社会天地,他的小说是以身边的小人物来透视人生和时代,更加重视心理描写,和最初的自叙传小说家郁达夫、郭沫若一样,他在感情上追求的,是忠实的率真态度。
一、散文化结构的写作
自叙传小说“在叙述上不重视情节或场景的经营,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倾向”①,小说的散文化其实是增强抒情效果的一种手段。史铁生也说:“散文正以其内省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一是因为散文的形式利于内省……二是因为一个散字,不仅宣布了它的自由,还保障着它的平易近人。”②的确,史铁生小说的散文化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与他一直以来的经验内省式写作有关。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而史铁生的叙事作品中往往隐含着作者本身的自我形象,他的叙事是一种个人化叙事的体现,他热衷于在小说里坦白的显露自己的声音,因此,散文化的小说体式可以帮助他充分完成他自己。其实自“五四”以来,小说便已有了散文化倾向,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都带有显著的散文化特点,小说的散文化让小说更加自由和随性,而在淡化环境、虚化人物、简化情节以后,情绪表现就会更加浓烈。
史铁生小说的散文化首先体现在环境描写上,传统小说的环境描写都是为了情节和人物服务,史铁生则不然,他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多了一份纯粹,因而呈现出淡雅与诗意的文风。可以说,他小说里环境都是为“自我”服务的,我写只是因为我想要写,不为其他。《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不时地穿插了对当地环境、风俗、民歌、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些描写出现得很随意,并没有起到塑造人物渲染气氛的作用,完全是因为作者想到了,它就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回忆跳了出来,跃然纸上。史铁生就像是一个讲故事的老友,他可以随时插话,但这丝毫不影响故事的完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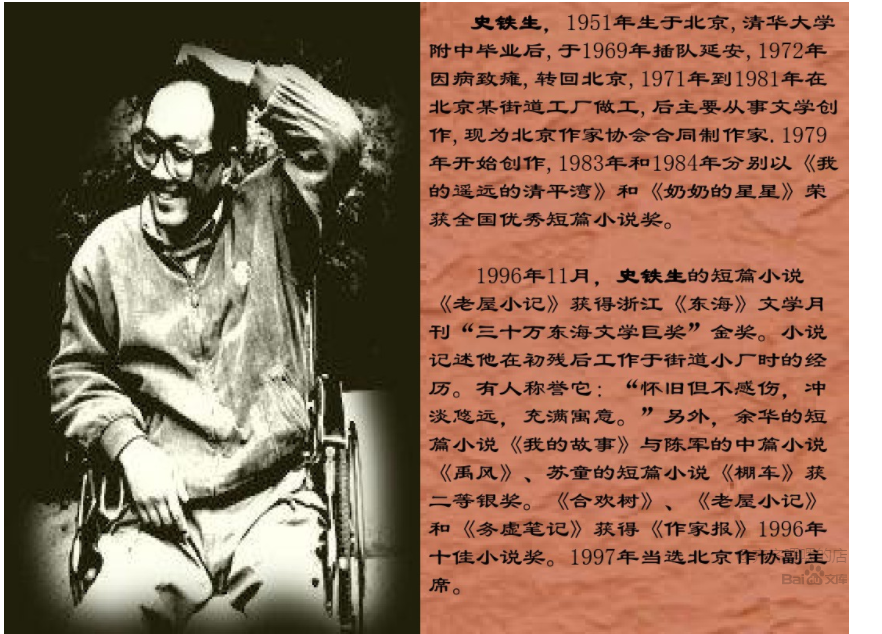
史铁生小说的“自叙传”性质研究
第二章 史铁生残疾主题小说的“在”与“思”
第一节 从“我的残疾”到“残疾的人”
作家应该去表现他所体验和感受到的生活,去写“自己的生活和与之长在一起的东西”②。史铁生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写作者,未必能够塑造出真实的他人(所谓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写作者只能塑造真实的自己。”③所以在史铁生的小说中,始终有一个形象十分相似的抒情主人公,同郁达夫反复描摹的余零者一样,这个抒情形象也是他反复确认的自我形象,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双腿瘫痪,渴望爱情,靠写作为生。生活和艺术就这样紧紧缠绕在一起,一方面是生活决定了他的写作题材,另一方面,写作也在改变着他的精神气质,而气质又直接影响了作家写作的风格。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不同于早期书写一己体验的小说,这时期史铁生的写作背负了更多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推己及人,他在小说里着重表现了残疾群体生活环境的严峻,社会对残疾群体的忽视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必须有人站出来,才能让这个群体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于是史铁生高声疾呼:“建筑设计师们可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是残疾人,我们上不去珠穆拉玛峰和台阶。”
一、残疾自画像
“自”在字典里的解释有自己、自我、本身之意,所以在自叙传小说中,“自我”是重点表现的对象。这个“自我”是来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的艺术形象,也就是郁达夫所强调的“个性”,它是一切叙事的基础。
史铁生在小说里塑造了很多残疾人形象,同样也都带着“自我”的意味。比如《夏天的玫瑰》里“我”是一个安了假肢的老头,“是半路残废的”②,漂泊半生,靠卖风筝为生,绝不给社会添负担,喜欢充满童心的孩子,在遥远的的故乡有一个深爱的姑娘;《白云》里的“我”是一个瘫痪的作家,头脑中都是千奇百怪的问题,心里藏着一个去了南方的故人;在《足球》中,“我”是摇着轮椅却依然无比热爱足球的山子或小刚;《我之舞》里的“我”是一个自幼学习很好,却还是因双腿瘫痪而找不到工作单位的十八岁青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到离家不远处的古园中消磨时光;《车神》里的“我”是一个摇着车走过许多艰难岁月,也一直被车神照料的人;《原罪·宿命》里的“我”是原罪章中一直被种在床上,只能靠一种盲目相信的精神活着的十叔,宿命篇里“我”是因一个狗屁而遭遇了车祸,从此只能瘫在床上靠写小说为生的莫非;还有《午餐半小时》、《老屋小记》、《没有太阳的角落》中在街道生产组工作的残疾小伙,《山顶上的传说》里遭遇退稿、痛失爱情、执着寻找“点子”的瘸腿扫地青年,《在一个冬天的晚上》里的架着拐的男子,《务虚笔记》里在徘徊在爱与性边缘的残疾人 C……这些人都不是“史铁生”,但他们在某些方面都不可避免的带着史铁生的影子,这种似我非我的形象,最突出的似我之处,就是无一例外的残疾。
.........................
第二节 从“残疾的人”到“人的残疾”
残疾主题被史铁生不断发展,反复变奏,逐渐走向深刻。最初他只是关注自己的残疾境遇,对个人命运的表现占主体地位,而后关注面逐渐转向整个残疾群体,小说重点探讨社会环境对残疾人生活的影响,最终他在残疾的人里看见了“人的残疾”。残疾既是残缺和阻碍,那名为人者,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当“残疾”一词具有了普适性,哲思开始显现。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思考也是史铁生“自我”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他十分注重自我的艺术化处理,即把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作为小说人物的行为准则,以达到主客观在某种程度上真实的统一。
一、寓言式的“我思”
学界一般以《命若琴弦》为标志来划分史铁生的创作时期,认为这是他的创作由“实”转“虚”的开始。其前期的作品多以表现生活为主,而后期则主要面向形而上的问题,多年来对于苦难和残缺的思考,确实使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变化。譬如《来到人间》、《夏天的玫瑰》等作品,史铁生旨在揭示社会现象,改善残疾人境遇,没有更多的触碰残疾与宿命这个终极命题,亦没有将其关心的范围扩大到全人类的福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还是能看到史铁生因无法改变命运而流露出的伤心失望之情。同样是残疾主题,在《命若琴弦》里史铁生对残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他开始接受残缺也试着承领苦难,既然残疾无法改变,人的限制也无法超越,何不将其视为一种馈赠,“没有痛苦和磨难你就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幸福”①。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理解,也由此衍生出了过程美学。
《命若琴弦》讲述的是患有眼疾的师徒三代人与一张空白药方的故事,这里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主人公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两个说书的瞎子。只要弹够一定的琴弦数,就可以获得重见光明,这样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实则体现了史铁生的生命哲学,“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②从《命若琴学》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史铁生小说中的写实倾向逐渐消失了,他采用了一种更隐晦的寓言式写法,文中的老瞎子和小瞎子看似离自身原型“史铁生”相去甚远,其实不然,残疾既意味着缺陷,那么眼疾与腿疾,世间的你与我,又有何差异,老瞎子曲折的求医问药史,也是史铁生心路历程的写照,只不过老瞎子靠说唱,而史铁生靠写作。在这篇小说中,盲人形象取代了以往的瘫痪青年形象,这表现了史铁生思想从“我”到“我们”再到“众生”的一个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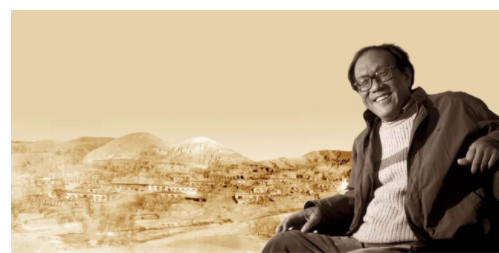
史铁生小说的“自叙传”性质研究
....................................
第三章 史铁生哲思主题小说的“行魂”之旅....................................42
第一节 “心魂自传”................................................ 42
一、叛徒:社会自我......................................43
二、爱情:个人自我................................................47
第二节 “写作之夜”.................................. 50
一、混淆与重叠...........................................50
二、独语与对话..................................................54
结语............................................. 58
第三章 史铁生哲思主题小说的“行魂”之旅
第一节 “心魂自传”
史铁生曾在给友人柳青的一封信中说,“在我想来,人们完全可以把《务虚笔记》看成自传体小说。只不过,其所传者不是在空间中发生过的,而是在心魂中发生着的事件。”②之后的一次采访他再次提到:“《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都可以说是‘心魂自传’,或者是‘心魂的一种可能性’。”③所谓心魂,就是“我”的内心世界,是“我”的欲望和隐秘,它们比实际行为大得多,超出实际行为的那部分,就是人的可能性。史铁生将他生命中隐而不发的那段心绪,那些可能,全在小说里实现,尽管常常表现为矛盾,但“善恶俱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是此一心魂的真确”①。这一阶段里“我”的形象不再是一个具像,而是一段段思绪,一种种可能。
一、叛徒:社会自我
史铁生后期的心魂写作,都指向一个终极之问——我是谁,他承认这是他生命的追问中一个核心的问题。笔者认为,生命固有的遗传密码或许可将其谜底揭开,这两条密码便是史铁生说的残疾与爱情,也可称为残缺与爱情。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区别出“我”的同时,也同样区别出了“别人”,于是人生而孤独,在亲密中感受着差别和伤害,这是个体化和社会化的双重残缺,处于这种残缺之中,我们因更渴望敞开和融合,而走向了爱情。所以“我”,必是在残缺与爱情的消息中等待识别。
“叛徒”是其心魂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残缺的象征,也是史铁生社会自我的体现。所谓社会自我,心理学家将其解释为,一定程度上,人对自我的认知是由集体认同所决定的。在史铁生看来,叛徒其实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类对待叛徒的态度出奇的统一,包括叛徒本人,他们将自己放逐在人类之外,永远活在恐惧和愧疚中,这是比死亡更残酷的刑法。小说《绵绵的秋雨》、《老人》、《两个故事》、《中篇 1 或短篇 4》等作品中都塑造了“叛徒”的形象,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还设置了专题来讨论叛徒问题。他提出,如何看待叛徒是认识人性的关键,这个一直让人嗤之以鼻的词,背后其实另有隐情,他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探讨叛徒出现的心理原因。
...............................
结语
自叙传文学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不断地分化演变,影响了其后很多作家的创作,史铁生可以说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他的小说在表现出强烈的“自叙传”特点的同时,更显示了明确的个人风格。
在早期创作中,史铁生选择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素材直接融入小说,“自我”与“真实”是其主要表现的两个方面;残疾主题小说的大量出现,意味着史铁生对“自我”的认识又更进一步,一个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瘫痪,心中必定有诸多的不平、痛苦和惊愕,痛定思痛,他借助残疾问题,逐渐拉开了生命哲思的序幕;以《命若琴弦》为标志,史铁生的创作逐渐脱离现实领域,走向更隐秘的心魂之中,这也许是一个必然现象,他坐在轮椅上的时间太久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却在日复一日的思索与追问中,洞察了自己甚至全人类的内心,因此写作手法也更加的多变。从中不难看出,史铁生的创作一直带有自叙传的性质,读史铁生的小说,我们总是能从中看到作家的投影,看到“我”的各种存在形态。这个“我”是灵与肉的统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研究史铁生小说的自叙传性质,实际上就是探讨史铁生书写自我的过程。
史铁生曾说写作对于他是一种命运,这命运最终指向了人之存在的根本问题,他提出“纯文学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因此它是超越着制度和阶级,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①,至此,史铁生已经超越了“自叙传小说”的题材格局和思想境界,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写作理想,也为当代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