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诗书写殊异
(一)英雄形象之别:悲剧气质与逍遥风度
“史诗永远是把重要的人物作为主人公,这个人物和很多人物、事件与现象发生联系和接触……通过这个人物,整个世界的宏伟壮阔都生动地显现出来了。”①由此观之,刻画出具有深刻意义的英雄形象是史诗写作的重要命题。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史诗甚至直接以英雄的名字命名,以此表达作家对其精神气质的高度礼赞。如《格萨尔王》、《嘎达梅林》等一系列著名史诗。史诗中塑造的英雄身上所具有的慷慨、勇敢、忠诚的气质使得读者深受感染,也寄托他们对理想人格的想象与追求。姜兆文与肖亦农作为蒙古族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的勇敢探索者和大胆的弄潮儿,母体的文化血液将他们的根脉深藏于汉域,但是他们的文学视野和思想观念早已漫出文化的界限,抵达了更深刻的境界。两位作家在双重文化的参考之下,既借鉴了蒙古族传统的英雄母题,又交接吐纳了各自的历史情怀,从而塑造了不同气质的英雄形象。
王富仁先生曾经对人物的悲剧性精神有过深刻的阐释:“人物的悲剧性精神,源自于其对人类、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困惑,即人类在面临重大困境时内心的冲突和关于自我命运的思考。”②也就是说人物的悲剧性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自我在二难选择之间对命运的反抗与斗争。姜兆文在塑造渥巴锡这个形象时,将其放置在众多尖锐激烈的冲突中,力图彰显出人物性格中悲剧性的张力。渥巴锡深层次的性格悲剧具体表现在背负的东归使命与强大的现实间的对立、爱情欲望与部落和谐间的对立、家庭完整与集体稳定间的对立。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姜兆文在作品中着力表现英雄人物在面对这些巨大冲突时的挣扎,以及沉潜在这些激烈的心理斗争之下人物内心的波澜。
..............................
(二)精神旨归之别:血缘宗法与现代文明
史诗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对民族斗争和时代风云的展现,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露以及对人类发展前景的预示,也就是说史诗有时甚至可以超越一个民族的既定历史,探寻和思索更为贴近人类本质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史诗的阅读,读者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历史风貌,因此史诗中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就尤为重要。
《东归英雄传》的深刻意义体现在从深邃悠远的文化积淀中探寻民族性格的烙印,从历史的高度梳理一个民族所延续的精神气韵和心理素质。《东归英雄传》取材于历史,作为一部反映土尔扈特东归历史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与描述人际关系时,站在了独特的历史背景上,较深层地开掘出独特的民族心理结构,从而使作品处处渗透出对血缘宗法观念的强调。
首先,整个土尔扈特部都是一个利用血缘关系维系的部落,舍楞既是汗国的重臣,也是渥巴锡的远侄叔父,策伯克多尔济作为汗国的重臣,同时也是渥巴锡的族侄,他们与渥巴锡都有双重的关系。其次,作品对于血缘宗法观念的强调还来自于作家对渥巴锡与阿萨莱这对父子关系的描述中,渥巴锡为了东归事业的顺利进行,不惜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俄国作为人质,儿子对于父亲权威的绝对服从,都体现了土尔扈特内部秩序井然的血缘关系。
较《穹庐》中松散的部落联盟,土尔扈特部落由血缘结构而成的组织更加严密,土尔扈特部在面对惨烈的战争时候能够同仇敌忾,结成强大的组织。当土尔扈特遭到毁灭性挫折时,部落内部的豪侠猛士们身上显示出来的忠诚义勇、舍身赴难的精神都源于强大的血缘关系和道德自律。在土尔扈特内部尽管同样面临着权力纷争,如策伯克多尔济作为土尔扈特部合法的继承人,虽然同样对土尔扈特的权力心有向往,但是在东归统一大业上,策伯克多尔济与渥巴锡的诉求却是一致的,因为整个土尔扈特部落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权力的得失。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渥巴锡身负重伤,策伯克多尔济才能够坦率地剖白自己:“一年前,我从不相信舍楞祖父大人会和汗王殿下心心相印,像舍楞祖父大人直到今天早晨还不相信我会‘背叛’女皇一样。当然,回想起我们长期的互相戒备的确叫人深感遗憾。”①
............................
二、原因探析
(一)个人经历差异
作家的身世及经历是进入其内心世界的第一把钥匙,有理论家这样界定作家的早期经验:“对于一个文学艺术家来说,丰富的早期经验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这些经历都是他最有个性最有价值的‘不动产’,它们会保持一生,并且在作家从事主观创造性活动时执拗地流淌和复显出来。”
姜兆文祖籍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1939 年 10 月 19 日出生在科尔沁草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丰赡的文学营养的滋养之下,孕育了姜兆文先生博识好学的性格特质。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1957 年即将高中毕业的姜兆文在“大鸣大放”的号召之下被迫辍学。个人在特殊年代里往往表现出力量的微薄,在政治潮流的裹挟之下姜兆文艰难立足,不得不奔赴青海参加劳动学习,仅一年之后,姜兆文又北上兴安岭劣的自然环境给他的身心带来双重考验,但是姜兆文从未放弃自己对于文学创作的执念。“在 14 年里,除了作了 8 年的代课老师,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短期的临时性劳动,或在深山采药、或在林海伐木、或在沙场装车、历经坎坷,九死一生。他对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有另一种看法,他认为很苦,但收获也很大。”①八年的中学语文教学经历,使得姜兆文在语法、修辞、古汉语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为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在早期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姜兆文踏上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道路。当时作为牙克石酒厂里的临时工,姜兆文全家三代五口人蜇居在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中,日常生活的琐碎甚至无法给他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微薄的收入仅能维持日常的生计支出,如此艰苦恶劣的生活条件并未浇熄姜兆文创作的欲望,反而激发了他向内探寻的激情。“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尝尽人生滋味,阅遍种种人面,促使他向内作灵魂自省,向外对社会进行思索,实为长篇小说的创作准备了条件。”②早期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决定了姜兆文性格中坚韧凝思的一面,他的作品也必然的会受到其性格的影响。《东归英雄传》中的渥巴锡、舍楞、色克色那等人,他们的性格中都体现出了深沉自省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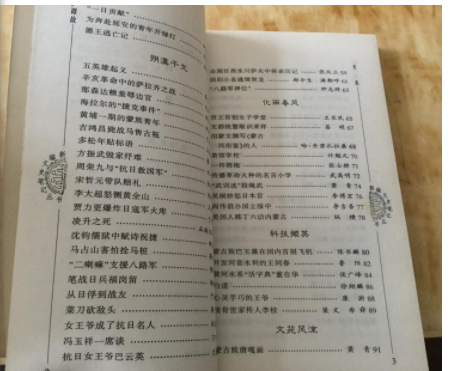
《东归英雄传》与《穹庐》之比较研究
(二)地域文化差异
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意识的表达,也是作家审美意识的体现,姜兆文与肖亦农通过对蒙古族不同部落东归历史的书写,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念,抒发自我的本真体验。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家精神品格的构建过程,而作家的精神建构又离不开本人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对作家来说“一旦进入现实的体验,一旦运用现实的体验作为写作的材料,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血的渗透。这种文化表现为本土社会、本土人生、本土语言的总和,也表现为本土文化与非本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成果总和。”①地域文化是作家进行创作源源不断的艺术动力,也是提供给作家本人创作营养的坚实土壤。综合理论家对“地域文化”的界定,笔者认为“地域文化”指的是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相交接融合,孕育培植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个性鲜明、异彩纷呈的自然环境是地域文化形成的背景,独特的环境熏陶出作家的感情依恋,并能进一步影响作家的道德体验、审美方式等。姜兆文的历史小说写作已经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探究其原因,这和给予他文化滋养,并教会他对历史进行深刻思考的呼伦贝尔大地密切相关。呼伦贝尔作为一块拥有野性魅力与蓬勃生命力的文化土壤,几百年来经济的多元共生,文化的繁荣并存是其无法忽视的显著优势。居住于此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人民进行着持续地交流与融合,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汉族人民也源源不断地与这片文化绿野互相融合。汉族人民在与少数民族人民的互相交流、频繁往来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游牧文明的影响。游牧文明剽悍、尚武的传统也必将深深地影响姜兆文的创作。“呼伦贝尔这块沃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创作,在长期与牧民的交往中使我浸染了呼伦贝尔人民质朴、豪放的性格特征。长久地融入草原民族、与少数民族人民频繁往来、共同生活的经历使我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了解了他们的生存状态,懂得了他们的感情和心理。”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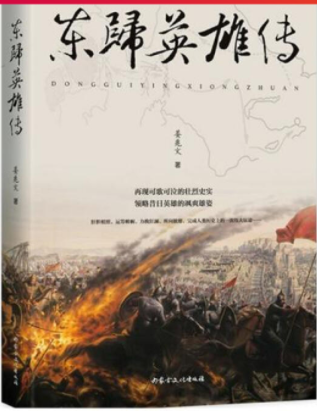
《东归英雄传》与《穹庐》之比较研究
..........................
三、价值评估.................................. 31
(一)历史小说的叙事向度: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得失.................................... 31
(二)“汉写民”文学的启示:跨族别的叙述立场选择............................ 34
结语.................................37
三、价值评估
(一)历史小说的叙事向度: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得失
“历史小说”是指以小说的形式讲述潜藏于时代之下悠久的往事。作家在历史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向度,一种是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书写,即“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历时地有规则地讲故事”①评论家将之称为“历史叙事”,另一种则是“侧重于虚构化地历时地有规则地讲故事”②也就是为大众所熟知的“文学叙事”。
姜兆文与肖亦农从历史文献中爬梳整理,跨越历史时空的隔膜,大胆地呈现了蒙古族不同部落的东归史诗,并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叙事类型。姜兆文对土尔扈特蒙古族人民的品格面貌和精神气度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在土尔扈特人民同仇敌忾的历史斗争中提炼出了中华人民渴望团结与统一的决心,与此同时作者还凭借着虔诚的创作态度,沿着时间的纵向延伸书写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以此达到纠史之误的效果。肖亦农则凭借大胆充沛的想象,合理地回望了布里亚特东归的历史,以文学的形式缝合了时间与空间的裂痕,让当下的读者可以通过文本挖掘历史、尊重历史。
西方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记载颇多,但多和真实的历史存在出入,如一些俄国史学家、民族学家在谈及土尔扈特西迁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于卫拉特各部首领们为进行领土扩张的目的。一些俄国研究者甚至认为“卫拉特是想重建昔日的成吉思汗大蒙古国。”③这种说法完全有悖于我们分析土尔扈特东归的爱国性和正义性。
...........................
结语
姜兆文以史性的沉重书写了土尔扈特艰难东归的历史,肖亦农则以诗性的轻盈展现了布里亚特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下的命运抉择,两位作家为我们拓宽了蒙古族史诗书写的不同思路。两位作家根扎在自己的母体文化中,又借着内蒙古这块文化沃土,将叙述的视野深入蒙古族不同部落的历史,为我们呈现出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东归史诗。与此同时,作为两位汉族作家,他们呼应了时代潮流,创作出了具有历史深度和现实启迪意义的优秀作品,也展现了中华各民族的平等交流与团结和谐的美好现实,通过两部作品的比较我们看到了蒙汉民族文学的平等对话,以及蒙汉文化的互相影响和共同发展。
当然无可否认,两位作家在进行跨族别、跨文化叙事的过程会有一定的瑕疵。如姜兆文先生在文本写作的过程中过于拘泥于历史的呈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文学性。肖亦农则在塑造人物角色时,偶也有违于正常的情感发展逻辑的片段。然而瑕不掩瑜,两位作家对于蒙古族不同部落的东归历史进行了细致的书写,将被掩盖的历史进行原生态的还原,不仅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历史的窗口,也为蒙古族的文学书写带来了新的气象。
两位作家抱着真诚、友爱的态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书写,强调文化间的对话与融合,其间自然也寄托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各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由衷关切。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部作品在文本言说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受作家个人的影响,但是两位作家借助土尔扈特与布里亚特的东归故事书写,都彰显出了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