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破旧立新:1980 年代“纯文学”话语生成的历史语境
1.1 时代规范下的文学制度建构与调整
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是建立在对由来已久的极“左”路线的反叛基础上的,以过去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作为对立的他者,建构了一个重新起源的历史神话。通过分析新时期作家及批评家对文学的思考及实践,会发现他们有意使新时期文学与“现代化想象”接轨的历史动力是文艺政策的改变,文艺工作者对旧的文艺思想及错误的文艺政策的反思在文学体制的话语规约下稳步前行。八十年代的“纯文学”话语并不是一个超历史的“本质”,而是在一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逐步建构起来的概念,因此考察文学的自主性过程首先要研究文学制度的演进和分化。正如陶东风、李松岳指出的,文学艺术的自主性的建构依赖于历史发展中的社会转型。只有笼罩在文学上空的极“左”阴影消散,文学走向自主才变得可能。八十年代的“纯文学”诉求的达成根本上还是归因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和社会目标的变革,重视“纯文学”建构的特殊社会语境才能超越一般化的经验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局限,对“纯文学”本身的考量也更具历史反思能力。
1.1.1 “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终结
1978 年 5 月 10 日的《理论动态》和 11 月的《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拨乱反正。告别僵化的思维惯性和庸俗社会学,倡导科学思维引领社会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国家的现代化想象。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国范围内的批判“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全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这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团结一致向前看,致力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成为了全国上下一致的目标。从历史转折的角度看,社会制度及目标的调整积累了思想文化变革的动能,不仅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而且会改变人们的审美取向。
..........................
1.2 从“伤痕”到“反思”:革命话语的“体系内批判”
“文革”结束后,中国作家怀着极大的热情呼应历史的变革。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一系列文学思潮及流派都致力于“人的复归”和“文学自身价值”的重建。在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前期,其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影响和轰动效应与五十到七十年代非常相似。新时期文学似乎通过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姿态重新回到了五四文学张扬“人”的个性的逻辑起点上,以“反左”和“反封建”为主要价值依据的现代性话语构成对过去激进文化的历史纠偏。对“人”自身价值的确立、恢复现实主义的辉煌、重拾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新时期”文学用直面现实的激情,开启了一段新的现代化历史运动。
1.2.1 话语激励与话语规约
“新时期”之初,以“伤痕”、“反思”小说为代表的社会性文学与社会政治变革和大众审美倾向达成一种巧妙的和谐状态,这是刚摆脱社会动乱、渴望开启新生活的社会环境使然,在文学创作上自发地“落实政策”,在文学体制的话语规范下进行内部调整。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伤痕文学”都被指认为新时期文学真正的起源,因为其致力于修复历史伤痛并承担了重建现实政治的功能。在以除旧布新为主潮的历史时期,伤痕文学通过展示极端生存环境下的人性灾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极“左”为特征的专制和蒙昧主义。在叙述那段非正常的历史时,“伤痕”作家重新对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进行确认,比如《伤痕》里的“妈妈”等被极“左”路线强加的叛徒身份是在新的政治语境下得以平反的,找回了曾经丢失的“革命”身份,而这正关系着作为“人”的价值回归和家庭伦理亲情的恢复。而《班主任》更是成功刻画了一个政治上根正苗红但思想僵化教条的谢惠敏形象,这一主体在思想政治上完美地无可挑剔,却也暴露了“四人帮”统治下一代青少年的愚昧与空心化。通过对“文革政治”培养的“新人”形象的颠覆,《班主任》实现了认知装置的转换,把张俊石老师塑造为一个拯救者的形象,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地位。虽然这其中隐含了深刻的文化政治,但也确实起到了颠覆“文革政治”的历史使命,建构了新的历史主体。
.........................
第二章 形式突围:1980 年代“纯文学”理念与“先锋”文学实践的相互缠绕
2.1“文学现代化”焦虑下的突围
新时期以来,很多理论家通过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对立面,来揭露其僵化、教条、非审美的一面,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文学的合法性。如果说刘再复是在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基础上发掘出了一个异于“十七年文学”的主体,那么鲁枢元则借用西方现代派资源引出了“向内转”的实际操作理论,“向内转”的叙述为后来的“纯文学”实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曾经的极“左”政治灾难在人民内心深处留下了严重的“内伤”,特殊历史时期狭隘地把文学理解为对社会现实政治“镜映式的”反映,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伤害了文学的自律性。经历浩劫之后的反省、忏悔心理为文学的“向内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家以一种叛逆式的姿态展现出个人内心精神的复杂性,深化对“人”自身的认识。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验的破产必然会导致作家重新寻找文学发展的出海口,远离政治的“现代化想象”催生了以“形式意识形态”终结“文学意识形态”的先锋文学。
“先锋文学”作为八十年代“纯文学”的代表,伴随着“纯文学”从一种反叛性的叙事话语到逐渐保守的文学观念,“先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也遭到重估。如何重述“先锋”文学的可能性,“先锋”文学是在何种意义上实现“纯文学”观念的诉求的,“先锋”之后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缠绕关系影响着我们对于八十年代文学观念及实践的反思。因此,在研究“先锋文学”的生成及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坚持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倡的“永远历史化”的原则,将“先锋文学”这一具有突围表演性质的形式革命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知识谱系的考察。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分析先锋作家与批评家的思想观念构造,这样才能更为接近历史的原貌,发现文本与历史之间巧妙的关联。
.............................
2.2 形式实验的极端探索
当代先锋小说不仅在叙事主题和内容上对传统的主流叙述进行了颠覆,用后现代的精神姿态消解了功利性的文学观,而且还以决绝的形式探索和语言实验完成了对现实主义写作规则的反叛。而必须重视的一点就是,形式不仅仅只是一种表现内容的技巧,而是克莱夫·贝尔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先锋小说作品中不断探索的新形式其实与内容统一在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之中,这种形式革命相对于以前的主流写作方式有某种“边缘”的意味,也选择了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先锋小说形式实践背后有一种“表意的焦虑”①,即面对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他们无法有力地介入当时的历史现实,转而用语言形式主义实验来表达个人经验,历史和现实都成了语言表述的附属品,这其中又有自主选择与被动安排的区分。从历史转折的意义来说,先锋文学的兴起无疑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更新与迭起,新的文学因素的产生表明了写作者观察与理解世界的方式与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也重造了整个小说的性质与功能,给予了文学写作者一个信号:文学也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凭借自身的艺术性生存。抛却了意识形态诉求的先锋文学似乎脱离了现代以来构造民族国家寓言的使命,给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旧有的文学观念及写作方法已是“明日黄花”,形式主义实验充当了文学转型的桥梁。
2.2.1 有意味的文学形式
1986 年号称“纯文学”刊物的《收获》连续几期推出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主流刊物的助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先锋派小说的影响力。谈论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形式实验,必然绕不开的一个作家就是马原,作为先锋小说潮流的探路人,他的走红顺应了文学变革的潮流,把“怎么写”的意义抬高到了比“写什么”更为重要的地位,终结了把语言作为工具和辅助的小说传统。小说语言及形式真正登上了当代文学的舞台,并扮演起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马原还率先在小说写作中有意识地探索远离意识形态中心的文体实验,关注审美形式的意义,并且借鉴了西方的元小说经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范式。“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①可谓是马原很多小说的叙事方式的缩写,这一特殊句型直接点明了小说这一文体的虚构性质。这是一个自我相关的句型结构,语法成分的互相缠绕本身就是打破旧有逻辑的明证,马原用语言圈套指明了小说虚构的本质。“马原的写作不再去建构时代的共同想象关系,不去讲述人们共通的愿望,写作变成纯粹个人经验的发掘,然而,也正因为此,马原不可避免地在自我的镜像中完成一次自恋式的绝对肯定。”②在马原的小说中,“马原”不再仅仅指示着作者的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作者构造的“自我”镜像,这个镜像拒绝了时代的体认,也不愿认同“他者”构设的共同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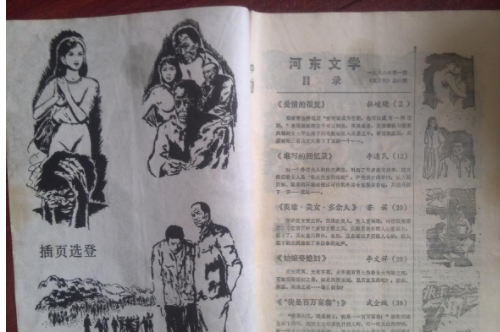
建构的文学神话 ——1980 年代“纯文学”话语的历史考察
第三章 “去政治化”:“纯文学”知识范式影响下的“重写文学史”实践 ....... 39
3.1 现代化想象和世界性视野 ............................................. 40
3.2 “审美原则”的价值与偏颇 ........................................... 45
3.3 “五四传统”与“重写”的反复 ....................................... 47
结语 ..................................... 51
第三章 “去政治化”:“纯文学”知识范式影响下的“重写文学史”实践
3.1 现代化想象和世界性视野
“文学性”问题在 20 世纪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被遮蔽已久,经由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乃至发展到极端的“文革文学”的一系列规训,文学的写作与评价越来越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失去了本身的自主性。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也影响到了文学评价,发现那些被某个时代、某个权威政治压抑的文学成了“重写”的目标。1980 年代中后期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潮流延续了八十年代初的历史重评与价值重估,并与现代性话语和世界性视野耦合,以其特殊的话语实践参与并形塑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活动,表征了知识分子参与历史书写的主体性。八十年代经过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的发掘,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启蒙、关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话语,“重写文学史”思潮实际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图景,影响了九十年代及当今的文化构成,很多文化事件的讨论都有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子,譬如 1994 年轰动一时的“经典大师排位”事件,把茅盾从文学经典大师库中剔除这一行为的背后是审美史观压倒政治史观的表征。以一种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重新考察“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能够超越于一般的理论认识层面,对以“文学性”和“历史性”为主导的文学史想象有更深层次的把握。
正如杨庆祥在《“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中所梳理、阐释的,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有两个策源地,分别是北京和上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开设也是分别由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学者组织开展,他们在提出新的文学史观时都得到了学界各种力量的支持与响应。杨庆祥不仅通过爬梳史料,考证“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历时性发展,而且还与历史的当事人进行对话,发现不同的身份意识决定了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把“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几位主将并置在一起考察,得到了以下结论:“如果跳出学科史的角度,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在时间上构成的线性递进的进程,而是一个可能在不同的空间里面都开始酝酿发生的‘历史思潮’,它一方面是八十年代社会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馈,另外一方面也是一批文学知识分子借助这一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和建设。”①可以说,北京和上海作为两个发源地平行地开展了以打破旧有学科史为目的的“重写文学史”活动,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书写活动中渗透了八十年代研究者的文学观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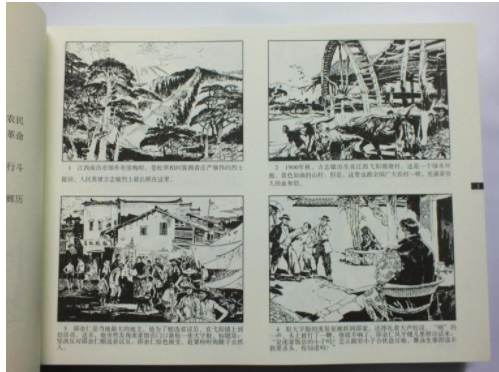
建构的文学神话 ——1980 年代“纯文学”话语的历史考察
...........................
结语
整理历史的过程会帮助我们明晰更多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特别是认识更多话语表述中含混的部分。作为一个在转折与断裂的八十年代中引起极大反响的概念,“纯文学”的生成、发展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当代中国追寻现代性的痕迹。它丰富了人们对“文学性”的认识,也促进了文学观念及写作方式的革新,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影响了写作者和读者的文学观念及审美趣味。
文学观念的发展与变革都与一定的历史语境相关,只有追溯“纯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命题,才能“遭遇”历史阶段的特定问题,考察它被建构的过程。这也是本文选择从“纯文学”的生成、发展这一角度进入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原因。一方面对“文学性”的认识促生了一代学者的文学想象与知识探索,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纯文学”的“幽灵”依然飘荡在之后三十多年的现实上空,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趣味和价值判断。“纯文学”理念留下了八十年代追逐“现代性”的理想激情,并且经由“纯文学”这一叙事话语,很多个人、无意识、自由、解放等命题都裹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还原八十年代自身的多重张力有助于我们对转折与断裂的历史时期进行去弊性的反思,不至于囿于一些本质主义的概念,从而获得一种历史性的认知。
八十年代“纯文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生成、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文学设法从政治意识形态中独立,完成它的自足性构想,这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进入以消费主义文化为主导的九十年代,“纯文学”所反抗的对立面由政治转向了市场,文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失去曾经的轰动效应。尤其在 20 世纪末,“纯文学”的主张已经形成另一种“文学史的权力”,耗尽了它所蓄藏的历史势能。八十年代刻意制造的文学神话又该走向何方,这成为研究者不得不深入反思的重要命题。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