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围绕“革命主体”问题展开的“革命文学”论争,在文学内部,摒弃普罗文学创作的弊病,丰富和发展了左翼文艺理论,进而开拓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内容和主题;在文学外部,促使左翼文学阵营形成广泛的团结,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迅速成立奠定基础,更为后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论争重点:关于“革命主体”的生成问题
(一)革命作家的文学“自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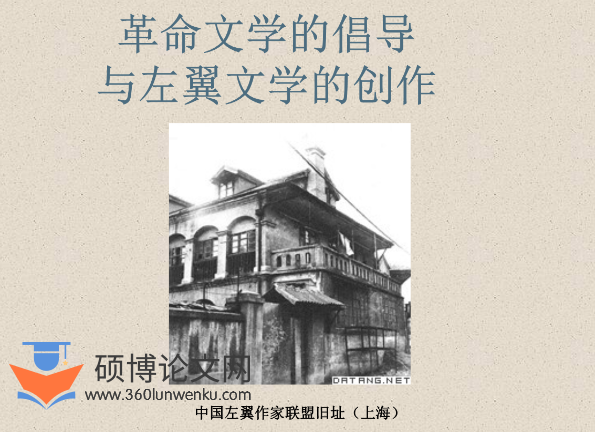
文学论文怎么写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七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先前在各种革命部门任职的知识分子被“抛出”[1]实际革命战场,切断了他们原来对于国家社会的畅想。被抛却了“革命主体”身份的知识分子必须思考如何重新参与将来的革命,如何进入将来的革命,以获得民族进步和解放。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意识到“要想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发展,就得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只有吸收这些群众积极参加斗争,才能形成一种足以打破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干涉者的力量,制止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消灭封建关系的残余,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为中国步入社会主义轨道创造过度条件。”[2]此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凸显出来。
在接下来的革命中,他们依旧希望在文学和革命之间微妙的关系之中找寻到作为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的位置。尽管“艺术自律”的调门从未停歇,然而,对于投入革命实际运动的文学青年而言,他们并不避讳自己的文学创造与政治意识之间的从属关系,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必须与革命保持同一方向,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作家可以以革命宣传人的身份,来实现其“革命主体”的身份追求,承担革命所赋予的时代重任。这时,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强调:知识分子由于其深厚的学识以及能力,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解和传输,进行从抽象到具体的文本呈现——他们可以作为“中介”,连接着无产阶级理论和工农大众。
“革命文学”的创作就是他们靠近“革命主体”的尝试。他们期望通过“革命文学”以宣传和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以激起工农大众反抗、斗争的情绪和行动,从而推动革命的发展,继续担任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得到极大的强调。在论争中,他们所讨论的“革命文学”的创作方式、创作主体等等问题,实际上就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如何成为“革命主体”的探索和思考,也是他们对于如何造成“革命主体”具体方式的分析。
...........................
(二)论争基础:域外理论中的“革命主体”
如若仅仅是国内的政治情况的变化,或许还不足以掀起这一场文坛的巨大风雨。域外理论资源的加入,使得这场论争多了一些国际左翼思潮的影响,不同域外资源在同一场域中冲击、融合,使得这一场论争展现出独特的风貌。中国的左翼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当时苏俄以及日本。
俄国“十月革命”像光一样照进黑暗中的中国,同时,他们文艺思想上的建设也给了中国的知识界以思考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方式。1923年的“苏俄文艺论战”中知识分子对苏俄文艺进行了集中的讨论,这给当时的中国以非常大的刺激。国内学习、思考苏俄文艺理论成为一时的热潮,有任国祯翻译的《苏俄文艺论战》;茅盾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介绍无产阶级艺术概念,同时对苏联创作和理论现状中的偏差进行批评、探讨;鲁迅于1926年翻译了苏俄文艺论战中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中专门说明“同路人”勃洛克的第三章,展示了托洛茨基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
蒋光慈早年在苏俄留学,对苏俄的文艺资源有着十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蒋光慈留苏期间,吸收了苏俄文艺论战中“岗位派”的观点。“岗位派”因主要阵地是《在岗位上》而得名,《在岗位上》在发表了《政治常识与文学的任务》,其认为凡是愿意为革命服务的文学家必须接受政治常识的训练。“如果文学的代表者不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文学就永远不会达到伟大时代的水平。”[1]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无限地接近革命,反映革命。以革命为材料和表现对象,这在蒋光慈的文章中反映出来。
............................
二、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革命主体的“灌输”与“思考”
(一)后期创造社:无产阶级意识“灌注”论
后期创造社李初梨、冯乃超等“小伙计”回国即扛起文化批判的大旗。他们创办《文化批判》,宣称“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1]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断:资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2]因而,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批判,这个批判是与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结合在一起的。
根据福本主义所提出的“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人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参与者”这一要求,创造社进行了生成无产阶级意识的努力。李初梨认为,如果仅仅依靠无产阶级直接地参与,则革命的水平十分低下,而只有智识阶级在批判中获取了无产阶级意识,再将这种意识灌注到无产阶级中,革命才能摆脱经验论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是一种以“灌输”的方式生成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灌输者”,智识阶级也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也是“革命主体”。这是因为智识阶级在其内部产生尖锐复杂的分化,而分化了的智识阶级广泛地接触着社会的和物质的生产过程,能够发见其生产的不合理性,可以生发出批判的要求,由批判的要求才可以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给知识分子在革命场上找到了合适的革命位置。——“武器的艺术”是掌握在能够进行全面的批判的知识分子手里的。由此,李初梨进行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主体”的确证。
................................
(二)太阳社:革命亲历者的“反映论”
如果说创造社是在理论上构想了“革命主体”的生成方式,那么太阳社则着重在创作方面将“革命主体”的生成演绎出来。太阳社认为,“革命主体”包含了参加过革命的“新作家”及其创作出来表现“革命现实”的作品。这就意味着,“革命主体”通过“反映”生成。
那么,问题便聚焦于“谁来反映”以及“反映什么”。其一是“反映”主体的问题。在太阳社看来,创作“革命文学”的主体,必须和革命保持高度的一致,有着深刻的党性。蒋光慈从生活基础论证了这一要求的合理性:作家与所处的时代有着深刻的经济、文化联结。旧世界的作家与旧世界有着深刻的阶级渊源,即使他们“在理性上已经领受了革命,而在情绪上,他们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旧的关系。”[2]而和革命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就不一样了——“他们自身就是革命”[3]蒋光慈的观点实际上受到了俄国“十月”派的影响。“十月”派对无产阶级文学纯粹性有着强烈的坚持,因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只能歪曲地反映革命”,无产阶级创作必须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完成。[4]所以,政治意识的纯洁性、是和党保持最亲密的关系是“革命主体”生成的必要条件:“还必须让那些愿意为革命服务的文学家同俄国共产党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因为如果不同这场革命的大脑、灵魂、原动力保持不可分的联系,那就不能完全地为革命服务。我们不相信,也绝不会相信’非党的文学‘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文学。如果文学的代表者不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文学就永远也不会达到伟大时代的水平。”
由此看来,“太阳社”作家具有实际革命经验、作品产出以及党员的身份。无疑是最能够代表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他们排斥被“旧时代”所滋养的“旧作家”认为他们无法真正地领受革命,写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因而,不能成为革命的主体。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明了地划分和说明新旧作家的队伍,但根据以是否参加革命,是否有阶级生成的革命情绪的判断来看,他们所指的旧作家就是“五四”时期的作家,而新作家就是太阳社这样系统接受过无产阶级理论亦或是参加过实际革命的作家。基于“革命主体”的自觉,太阳社在文本之中,塑造了一个个阶级革命的“战士”,展现阶级的意识和阶级的行动:《女俘虏》中主人公被问到名字时回答“我们的名字都是一样”[2]表现出阶级群体的坚定凝聚力量;蒋光慈《少年漂泊者》借汪中这一形象表现工人的力量和觉悟,展现出工人受到压迫之时,有着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勇气,迅速组织起罢工运动。也就是说,作为唯一的在文艺上的“革命主体”,太阳社作家们根据自身与革命共同成长的经验创造文艺作品,展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面貌,其文艺作品也表达了新作家所努力追寻的无产阶级意识。以图鼓动起革命,发挥和实际的革命家相似的作用。
............................
三、鲁迅和茅盾:“革命人”与小资产阶级的“中介”作用 ...................... 21
(一)鲁迅笔下的“先驱”与“众数” ........................ 21
(二)茅盾从“个体性”到“阶级视野”的扩充 ................... 24
四、生成“革命主体”的创作尝试 ................. 28
(一)《咆哮了的土地》:“革命文学”的多面尝试 ..................... 28
(二)《子夜》:左翼文学的开拓 .................... 31
结语 ............................. 37
四、生成“革命主体”的创作尝试
(一)《咆哮了的土地》:“革命文学”的多面尝试
“革命文学派”以冲破一切的话语展示着阶级理论的巨大力量,其推动了阶级理论的广泛传播。在论争的过程中,他们吸收“老一派”作家的观点,对“革命主体”有着更加深刻和明确的认识,这在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得到体现。
首先是表现了“革命主体”生成的艰难以及复杂性。早期的“革命文学”中,创作者将工农塑造成受压迫的、善良的底层群像。以“完美的受害者”的面貌说明其“革命主体”生成的必要性。然而,无差异的群体面相形成公式之后,会造成枯燥的阅读体验,而且文本中无产阶级面貌失真的展现,弱化了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蒋光慈显然意识到了这一弊端。在《咆哮了的土地中》中,他通过呈现农民面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展现革命之路的艰难。如固执的农民王荣发、拿自己老婆出气的吴长兴等等。他们并非是典型意义中坚韧奋斗的形象,相反的,他们有自己的特质。有粗野的一面,残暴的一面。例如吴长兴:“一切都使吴长兴气愤,而这气愤却找不到发泄的地方。命运捉弄得太厉害了,改变了他的神经的常度。他觉着一切都是他的仇敌,一切都使他气愤,这气愤总是要发泄的,于是他的老婆变成了他发泄的对象。”[1]这是一个被阶级剥削压迫得生活难以维持的弱者,向更弱者(妻子)的发泄。在这个层面上说,他是一个残暴的、粗鲁的农民;而刘二麻子在办农会之前跪在神像面前祷告
“威震八方的关老爷!兴汉灭曹的关老爷!你是古今忠义之人,请你暗地显灵帮助我们办这农会,好教我们穷人不再受有钱的欺负才好。我刘二麻子活了三十几岁,从来没有走过好运,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我可要请求你忠心耿耿的关老爷可怜我,保佑我,我一定多多地买香烧给你老人家……”
刘二麻子祷告至此,便恭恭敬敬地伏下叩了一个头,这使得立在他旁边的张进德禁不住发起笑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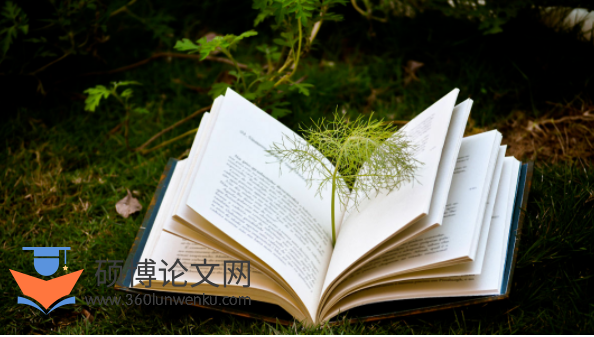
文学论文参考
............................
结语
“革命主体”的讨论,使得论争尽管呈现出尖锐、激烈的话语,然而对于“革命主体”的理论探索,知识分子的革命思考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革命主体”的生成问题得到了更多的交汇、融合。一方面,论争各方发见了自己理论的不足,这促使他们更深入地进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学习。“革命主体”的生成,不仅仅是单面的理论,而是要切实地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个体革命经验以及中国革命实际的融合。后期创造社提出的“意识输入”的阶级理论在论争后得以更大的传播,影响了鲁迅、茅盾等对“革命主体”生成方式的思考;太阳社也在论争中意识到自身理论的朴素性,开始学习“新写实主义”理论,逐渐摆脱了前期理论中“反应论”的束缚。鲁迅在论争中被“挤”着“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1]鲁迅在两个社团的直接攻击中,进入理论探索和翻译,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中,翻译《苏俄的文艺政策》连载于第一卷1—5期,并刊出《H.伊勃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增刊》《莱夫·N.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刊》等相关的理论讨论,同时,还集合了《壁下译丛》等翻译集子。在这翻译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了阶级意识的力量,扩展了对“革命主体”的认知。可以说,他们在论争之中逐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尽管双方依然有难以弥合的矛盾,但这是在承认阶级文艺理论的共识之下的冲突;茅盾在论争之后写出的《关于“创作”》以及《“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体现了唯物主义理论的学习……这些,都使得“革命主体”生成的理论具有更多言说的可能。
另一方面,对“革命主体”的讨论扩展到论争外部,许多向往革命的文学青年,通过创作、理论清理等方式探讨“革命主体”的无限可能。如刘一梦的《失业以后》,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革命(罢工)就意味着工人没有收入,罢工的失败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革命并不是一了百了的方式。在光明来临之前,需要面对巨大的重压和黑暗,“革命主体”的生成,在时代的神圣风潮之下,是具体的个人的压力和抉择;而在“左翼”之外的作家戴望舒,则尝试以“同路人”的方式进入“革命主体”,他翻译了《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以及“同路人”伊凡诺夫的《铁甲车》等等。他对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有着深刻的了解,然而,他并不意图靠近革命实践,而是以文学家的视角和眼光,审视“革命主体”生成的理论空间,意欲做革命的“同路人”。可见,不断扩大的讨论使得更多的作家开始审视“革命主体”的生成空间,对语义上的多义性进行辨析和讨论。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