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韩松科幻小说中的空间
1.1 身体作为元空间的社会文化批判意义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将身体视为“原-空间”,即最初的空间,身体天然具有空间性。身体还是空间产生的条件,“对我来说,如果我没有身体,就根本不会有空间这种东西。”②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存在,才有了“这里”和“那里”的区别,才有了上下高低深浅,身体使空间得以产生并形成意义。本部分将从身体切入,分析韩松的小说中作为元空间的身体是如何被规训、被阉割甚至被吞噬。
1.1.1 知识-权力对身体的规训
在福柯看来,空间为权力产生作用提供了场所,权力、知识通过对身体的区隔、监视、宰制,使得权力内化到身体空间,制造出“驯顺的身体”,于是人丧失了反抗意识,成为被权力规训的人。这种通过改造身体来规训意识的做法可以在韩松的长篇小说《医院》中得到清晰的展现。在“《医院》三部曲”中,主人公杨伟在出差所居住的宾馆里喝下一瓶矿泉水后腹痛难忍,被服务员送进了医院,如果说候诊大厅里大排长龙的挂号队伍、扬声器此起彼伏的轰鸣、划分精细令人眩晕的科室以及医生冷漠而威严的面孔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是我们熟悉的现实世界,那么腋下结满蛛网的候诊病人、墙壁上在褐色蘑菇里跳跃的透明老鼠、被改造为巨型医院的城市则让我们从日常经验中拔出脚来,迈入韩松为我们构建的科幻世界,进入他所虚构的文本空间。
在这个世界中,通过一场医药革命,我国进入了新的时代——药时代。医药革命是直接针对人本身的革命,因此药时代是对整个人类升级换代的时代。在药时代,人人都是病人,一个人从还未出生时就要接受治疗,首先通过基因测序检测胚胎罹患各种病症的几率,然后用健康基因替换异常基因,进行重组。而经过基因重组的婴儿与父母在生物学意义上已经不构成遗传关系,于是家庭关系被取消了。但是即便有经过改造的完美基因,疾病仍然存在,因为人工合成食品、病毒基因异变以及糜烂的生活方式、愈发恶化的生存环境仍然在侵蚀着人的身体。于是人们继续涌向医院,在医院中渡过被治疗的一生。“医院不仅能治躯体的病,更可以净化人的灵魂”①。先进的医学技术成为围困身体的工具,而被驯服的身体成了思想的牢笼,人的思想也随之被规训,没有人想要逃离,也无法逃离,因为对于这些病人而言,一旦离开医院,就意味着离开先进的医疗技术,意味着发病的潜在风险,尽管医院不过是延长了临死前的痛苦。
..............................
1.2 地铁作为地下空间的心理象征
“空间转向”后,空间成为具有多维面向的复杂概念,如果说韩松通过“身体”这一空间主要表现出空间的社会文化批判意义,那么本节则主要通过“地铁”空间考察其空间的心理意义。既然人的身体是元-空间,人必须生活在空间中,同时人又可以通过社会实践生产空间,那么空间必然与人的空间经验息息相关。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从现象学出发分析了一系列空间原型,如家屋、阁楼、地窖等,而这些空间意象往往引起人类某种相类似的空间感受和心理体验,如家屋给人的感受往往是一种安全感、幸福感,而地窖“作为家屋的阴部存在”,“分担了隐藏在地下的力量”,“当我们在地窖里做梦时,我们跟深渊里的非理性相互呼应协调”①,它使人感到恐惧、威胁。在本小节我们主要分析韩松“轨道三部曲”中的《地铁》,探讨在地铁作为地下空间是如何表征韩松的心理,将他的心理状态具象化。
《地铁》共分为五部分,分别讲述了五个故事。在第一个故事的开端,韩松先勾勒出一幅末班时分颓败恐怖的都市景象:“漆黑的月亮下面的城市,竟若一座浩阔的陵园,建筑物堆积如丘,垒出密密麻麻、凹凹凸凸的坟头,稀疏车流好似幽灵,打着鬼火,在其间不倦游荡”。而他笔下的地铁,更是鬼气弥漫,“他加快步伐,趔趄走下巨冢般的站台。是在回家,还是在迈向死亡呢?——深藏不露的地下世界营造出棺椁般的冰冷感。站台上还有一些候车人,荒原上的墓碑一样,歪歪斜斜插入地面,扣紧无脂青色嘴唇,仿若正在灵魂出窍。”当“墓碑”们进入地铁后,“均木鸡般坐着,又犴狴样面目狰狞”②。这正是韩松眼中的地铁,即便是早高峰拥挤的人群也不能祛除地铁中四处萦绕的森森鬼气,“‘遇到鬼了!’女人吐着紫白的舌头,低低咆哮,那样子使周行想到《聊斋志异》中的狐妖。”③如果说前两个故事还有日常生活的介入,冲淡了地下空间的恐怖张力,后三个故事则将时间设置为未来:被酸雨侵蚀的末日世界,丢失记忆的主人公在地下世界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宇宙真相,然而真相扑朔迷离,犹如深窟之中的幢幢鬼影;末日之后的地下世界,已经退化的人类渴望追寻丢失的地上文明,却发现早已被地上文明视为异类;更久远的未来,人类乘银河列车来到地球,在被老鼠侵占的地下世界中孤魂般游走,试图了解民族的过去。韩松曾在谈及《地铁》这部小说中说道:“在我的内心中, 地铁代表了一种变异、 速度和一种巨大的压抑, 很难从中摆脱, 而不得不去适应它。 在这种狭小、 拥挤的空间里, 要面对人与人相处的恐惧; 然后在黑暗的世界里奔行, 这本身就带来一种很大的恐惧感, 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意外。”①因此,地铁被韩松塑造为一个幽闭、黑暗、混乱、恐怖的地下空间,在这个地下空间里,人类如此急切地寻找,却又表现为对自身处境的麻木,对他人存在的冷漠和敌视,犹如虫豸一般在食欲和情欲中翻滚,最终被地铁载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
2 韩松科幻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结构
2.1 同心圆结构与叙事迷宫
2.1.1 同心圆结构
龙迪勇提出一种“中国套盒”式结构,指的是故事中套故事的小说结构,如《一千零一夜》、《十日谈》,都是由一个主要故事生引发出几个其他故事,并且产生不同的叙述者,在现代小说中,不同的故事之间会相互干扰、补充,彼此插入和并置,从而使作品作为整体得到加强。这里提出的同心圆结构与中国套盒有相似之处,都表现为丰富的叙述层次,但韩松的小说并不是在故事层面的并置,而是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的阐释,从而形成主题层面多种可能性的并置,我们将之命名为同心圆结构。
在小说《高铁》中,对“我是谁?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追问是推动情节不断发展的动力,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勾勒出世界的多种可能性,从而形成谜底上的层层闭环。小说第一部分以一场高铁事故为叙事原点,主人公周原从昏迷中醒来,发现父母已经伤亡,妻子不见踪影,而高铁还在急速行驶,在车上病友们无形的压制下,周原被迫开始在高铁上探索事故真相。手持锋利小斧头的舞器(谐音“武器”)使他了解到高铁不是在行驶,而是在以宇宙级别的尺度在膨胀,技术手段已经失灵,为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必须发动长征前往光年外的驾驶室;飞船设计师万户则告诉他高铁膨胀源于高铁脱离了技术人员与计算机的控制,拥有了意识,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必须凭借技术力量建造飞船逃离高铁,乘客不过是乘务员创造的人工智慧生物,所有的记忆都是幻觉;赤县却说种种违背物理规则的现象说明高铁是神造物,只有信神才能获得拯救;突然出现的列车长左手持十字架,右手握小斧头告诫大家要安分守己,停止探索,以繁殖为生存目的,将一切问题留给后代考虑。而每一位解释者都有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那就是《读书》。《读书》时而是消遣读物,时而是技术手册,时而是《圣经》,时而是春宫图,可以说频频出现的“《读书》”意象,不断地为主人公揭示出所谓真相的多个面向。但是对于这些在高铁中苦苦追寻真相的人来说,“也许还有一本书,永远无法看到了。„„没有人能掌握所有信息,没有人能看清列车全貌。连近似也不能。”①关于世界的解释重重叠叠,一个出现覆盖另一个,又被下一个新的解释所覆盖, “真相之外还有真相,答案后面还有答案”② 。“也许所有世界之上,还有一个总世界„„有时我又觉得,世界本身也许就是假的,它从来没有存在过——包括我们自己。”③彩色玻璃的后面是外面的世界,细菌内部的一个微点中藏着另一条时间线上的世界,高铁外面可能是海洋,可能是真空,甚至可能是集便器,可能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场游戏,世界的终结不过是为下一次世界末日提供模板„„世界之外还有世界,大世界套小世界,形成一个同心圆的结构。
................................
2.2 圆圈式结构与符号化人物
2.2.1 圆圈式结构
所谓圆圈式结构,是指打破线性叙事,将过去、现在、未来衔接成一个圆,表达时间的停滞与往复。王瑶认为在认为韩松文本中存在一种元叙事:“那是一种不断回到原点的“环舞”,是围绕同一意象的两种反向运动,并最终形成闭合的圆环。”①如在《逃出忧山》中,为了挽救婚姻,韩愈和妻子决定去曾经邂逅的忧山故地重游,到达忧山之后,突然之间时间静止,人烟全无,最后甚至连妻子也消失了,在火焰的灼烧感中韩愈从实验室中醒来,发现忧山之旅只是一场大脑实验,然而恰在此时,妻子给他送来了前往忧山的车票。故事以前往忧山开始,又以前往忧山结束,形成圆圈式结构。蕴含其中的是韩愈对世界的怀疑,忧山的困局究竟是真是假,“那声音”说世界不过是韩愈在脑中虚构的假象,是真的吗?他自己究竟是世界末日后唯一留存的一个意识,还是一个平庸凡俗的小人物?重重疑问藏在圆圈式结构里,作者不予解答。再如《高铁》,探险者阿辉在列车上的行程也是一个圆圈:第八车厢(原点)——餐车(僧人占据)——硬座车厢(过渡性质)——更多的车厢(梦游一般)——第八车厢(终点)②。与线性叙事不同,在阿辉的探险过程中,他并没有获得任何关于高铁的真相,相反,在一个接一个的车厢游历中,阿辉逐渐陷入更为扑朔迷离的迷宫之中。
在韩松看来,时间仿佛是一条衔尾蛇,自己吞噬自己,自己生产自己,在一个闭环中自我循环。在“轨道三部曲”中的《轨道》中,这部原本命名为《末日》的书讲述的是主人公所经历的世界末日,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青春的呻吟”从世界末日倒计时七天开始叙述,通过“我”对真相的探寻描绘出末日时代疯狂的众生相,然而故事却在倒计时三天时戛然而止。小说进入第二部分,再次从世纪末日倒计时七天开始叙述,一切又回到起点,“我好像从一个梦中坠入到另一个梦中”③,世人仍汲汲于权力、利益,浩大的娱乐活动席卷了末日世界,真相却在重重迷雾之外。终于在第三部分“宇宙的幻灭”中,末日到来了,然而这不过是为下一场世界末日做准备。原来宇宙不过是一场戏剧,生与死、重生与毁灭不过是剧作家纸上的符号,“只要他动笔写,一个接一个的世界便不断从虚空中咕噜噜冒出来,经历进化,最后走向终结,又在废墟上重生。就像舞台大幕升起又降落、降落又升起一样,从序幕到中场,到高潮,到尾声,尾声结束后又开始新的剧情。”①如同衔尾蛇一般,剧作家创造了世界,剧作家又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被自己所创造的角色拯救和统治。整个世界被安放预定的轨道上,轨道向前无限延伸,最终又回到原点,而被安置在预定轨道上的人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既有的命运,所谓真相,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文学类毕业论文参考
3 韩松科幻小说的空间叙事技巧...........................32
3.1 空间与时间...........................32
3.1.1 幽闭空间与时间循环...........................32
3.1.2 时间跳跃与空间转换...........................32
4 对韩松科幻小说创作的反思...........................32
4.1 韩松空间叙事的目的:指向现实...........................32
4.2 韩松的创作:以科幻小说为方法...........................32
结语.....................48
4 对韩松科幻小说的反思
4.1 韩松空间叙事的目的:指向现实
我们知道,任何一本小说都是对一个世界的独特建构,当我们沉浸于一篇小说时,我们说自己脱离了自己当下的现实空间,“进入”了作者所营造的独特的文本空间,因此,任何叙事作品都存在空间建构的问题。在苏恩文那里,科幻小说因其“间离”策略而与现实生活区分开来,也与那些强调真实性、经验性的现实主义文学区分开来,因为科幻小说更强调陌生化、虚构性。科幻小说试图建构的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在科幻文学结构的疏离设定中,时间和空间属性最重要也最基本,这两者可以决定科幻在何种程度上的科学真实和与现实世界疏离的远近”①,因此可以说,特殊的时空设定是使科幻世界陌生化的前提,它是科幻小说的典型特征,也是必要的叙事策略。并且在时空设置上,科幻小说比之其他类型更具有优势。在时间这一层面来说,唯有科幻小说能“穿行于一切可能的时间之中”,因为自然主义文学(包括现实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通俗文学)关注“经验的时间”,对于未来只能以梦、预兆等方式呈现,其他超自然主义文学则“回避了历史时间”,比如“神话定义在时间之上,民间故事被置于超越时间的传统的语法上的过去时”②。同时,科幻小说的创作也与人的时空观念息息相关,以空间观为例,在交通不便的前现代时期,科幻小说将空间设置为遥远的海边小岛,当地理大发现填补了地图上的每一处空白时,科幻小说中充满了凡尔纳式的异域风光展览,或者是月球占领、火星战争这种带有殖民主义的扩张心理,信息时代的网络空间则为科幻小说增添了赛博朋克这一子门类,在闪耀的细雨中和数据巨网中游荡着威廉·吉布森笔下那些疯狂的、带有自毁倾向的黑客。不过,苏恩文一再强调,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科幻文学“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就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出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一种拟换作者的经验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结构。”③即无论科幻小说中所建构的时空如何新奇怪异,它总是对现实时空的变形,是有限制的陌生化,因为陌生化的本意是“在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现实面前高高举起了一面令人震惊和间隔距离的镜子”①,“间离”作为科幻小说的写作技巧,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认知”,我们日常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种种呈现变形的时空中,带给我们以新奇感,陌生化的时空令我们震惊,从而延长了感受和思考的时间,令我们获得了对现实世界更为本质的认知。苏恩文因此发现了科幻小说的现实批判意义。按照苏恩文的理论路径,我们发现,韩松的科幻小说创作同样是认知与间离两项要素的相互交织,通过其有意的空间建构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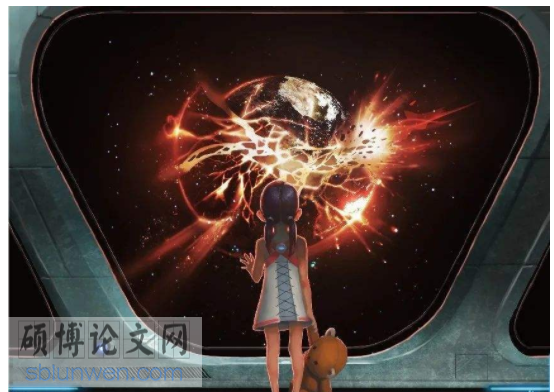
文学类毕业论文怎么写
.........................
结语
正如在开篇所说,韩松的科幻小说具有风格的独特性和主题的多义性,对于阐释者来说既是宝藏也是挑战,有研究者从文学史的角度切入,或分析韩松与鲁迅所代表的启蒙文学之间的继承与变革,或分析韩松与 80 年代先锋文学叙事之间的因袭与流变;有研究者从其独特的风格入手,探究其奇异的语言表达、奇观式的场景描写、碎片化的情节连缀;有研究者挖掘主题,或将之与杰姆逊的“民族寓言”相联系,寻找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寓言式表达,或从文化入手探讨其对伦理的僭越、对吃人文明的揭发,或将之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追寻韩松对理性和意义的消解,以及在荒诞之中安顿存在的种种努力和挣扎„„每一位研究者都为韩松的科幻小说研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则试图凭借空间叙事理论,对韩松的科幻小说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韩松科幻小说文本的独特之处进行回应,揭示了其文本中叙事迷宫、符号化人物和奇观式描写形成的原因,以及文本中诸如“地铁”、“医院”等空间的象征意义,同时也针对文学界对韩松科幻小说创作的批评对空间叙事进行反思,空间叙事理论的确打开了一条通往韩松叙事迷宫的路径,但不可否认,仅依赖空间叙事结构,并不能对碎片化文本进行有效整合。具有空间形式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是一项阅读挑战,因为它使得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不断地被打断,又使读者不断地试图在脑海中重新建构一个完整的文本空间,并接受其被再次打破的必然走向。也许对于研究者来说,这反而给阐释带来了多种可能,文本成为具有无限丰富谜底的谜题,可是也要提防将文本阐释变成一项丢弃了文本分析本身的智力竞赛。韩松的科幻小说具有多义性和含混性,本文在借助空间叙事理论进行文本分析时有时难免陷入理论的泥沼,希望在有限的字幅内,凭借有限的学识能力,能尽量将韩松科幻小说的独到之处和精妙之处阐释清楚,并不沦为理论的跑马场。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