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喀什汉语文学创作队伍
第一节 汉语文学作家构成
丁帆将西部的文人分为三大类型,即土著作家、流寓作家、客居作家。这种划分其实就是按照作家们生活在西部的时间长短来确定的。世代生存于此的就是本土作家,创作与西部密切相关的作品,记录生活的点滴。当然对流寓作家的类型也按照不同原因进行了细分归类。针对客居作家是最为容易划分的一类,以旅游、探险为目的稍作停留的作家,留下瞬时创作的关于喀什见闻的作品。另外,新疆学者夏冠洲将新疆汉语作家归纳为“‘由新疆起步的’、‘在新疆长期留驻的’和‘来新疆作短期旅游与访问的’三类进行概观性综述,较全面地总结了新时期新疆汉语文学的成绩。”①高戈将边塞诗人分成了三类,即‘行吟诗人’、‘羁旅诗人’和‘土著诗人’,这种划分和丁帆的划分是一种类似的划分类型。此后,王敏对新疆新生代作家做了“土著、移民、流寓、移居、网络”五分法归纳。②鉴于本文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结合丁帆、夏冠洲、高戈、王敏等相关划分类别,根据新时期以来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群体以移民、流寓、旅居为主的现实情况,对新时期以来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群体大致划分为两支主要队伍:本土作家和羁旅作家。
一、本土汉语作家——继往开来的主力军
偏安西北边远地区的喀什,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尽管这里气候干燥,却因西部高原冰雪融水的滋养灌溉出文明,凭借处于贸易交汇的位置和重要性,尤其是在当前发展背景下,喀什在经济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的经济日益发展,喀什地区在党中央与内地省市的关怀下抓住机遇不断奋进。经济上的差距并不能阻碍文学这一精神领域前进的步伐,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或作短暂停留的汉语作家,用他们的言语和方式书写着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通过长时间的留心观察,透视深藏在他们内心的情感。喀什本土汉语作家不仅为喀什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喀什本土作家的作品也为新时期以来喀什汉语文学的繁荣做了不懈地努力,是新时期以来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另外,作为新疆的历史文化名城,喀什不只是这样一个多元交汇的地区,更是一个容纳不同的地区,它的这种包容性为喀什本土汉语文学创作队伍的成长、发展提供了保障。喀什本土汉语文学作家除却少数是土著作家之外,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纪垦荒移民、支边、文革期间流放人员及其后代,他们定居于此,扎根边疆,成为喀什和喀什汉语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喀什本土汉语文学创作队伍的总体构成上看,喀什本土汉语作家的结构比较有层次。通过对喀什本土汉语文学作家的梳理,可以发现喀什本土汉语作家可以按照出生在解放前、文革前和文革开始后三个阶段进行划分。
.....................
第二节 汉语作家的创作成就
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喀什本土汉语作家作为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其创作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取得的成绩也较为突出。无论是创作团体的层层延续,还是作品类型的多样化;无论是本土作家,还是羁旅作家都在改革发展的背景下,为推动喀什文学进入新境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本土汉语作家的成就
新时期以来,喀什本土汉语作家以新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不同阶段的作家通过不同的作品展示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发展。老一辈的喀什汉语作家大多见证过共和国的建立、经历过新中国的曲折发展,也遭受过左倾思想的迫害,复杂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对历史、社会现实和文化的思考更加深刻,在表达上更加成熟。 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队伍中,在相互交流和学习中,通过社团、个人等形式建立刊物,为本区作家提供舞台,同时也培养一批文学新人。“截止 1990 年,喀什地区文联、文化处和作协、编辑部加强了与作家、业余作者的联系,通过各种途径,召开过多种形式的文学研究讨论会和报告会,提出了创作任务,调动了广大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扩大了创作队伍,地区作协接受了各族会员 200 多名。此外,还有一大批会外的业余创作队伍。一些文学爱好者,自发组织文学社团,出版由赵力、李宏、潘继鹏撰写、编印的文学刊物《脚印》等。”①虽然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内部刊物纷纷停刊,作家们的作品发表受限,但在这一阶段这些刊物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为喀什本土汉语文学发展进行新的探索与发展提供了场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青年作家搭建了创作的平台。此后,由于作品传播范围有限,很多喀什作家开始走出去,向外地发展投稿,也获得一定的认可。还有些本土作家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坚持不懈地发布作品。
......................
第二章 喀什汉语作家创作主题分析
第一节 生命意识的表现
袁行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说:“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事物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感”。①前半句强调作者头脑中的意象,后半句强调已经在文本中主观化的意象。但无论是作者头脑中的意象,还是文本呈现的意象,都是创作主体与客观载体之间相互交融的结果。同样,休谟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把所有存在物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思想倾向,并会把他们熟知的、他们直接感受到的那些性质转移到每一个对象之上”,②生存于喀什的汉语作家把他们对生命的体验与生命意义的认知投注于喀什这片自然与人文构筑的意象空间,将他们强烈的生命情感寄托在自然意象生命状态的表现上。
基于此,喀什汉语文学作家把写作转向自己生活和游历过的土地,从纷繁的世界中挣脱出来,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审视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生命的意义,大自然成为了他们情感和思想依托的载体。大漠、胡杨、红柳、骆驼刺、马、鹰等,不仅仅是一种可供观赏的自然景观,而且成为生活在这里的汉语作家对生命意识的一种映射,对自我的一种观照。正如梁漱溟所说:“自然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可分从两方面言之: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不可一息或离,人涵育在自然中,浑一不分,此一方面;其又一方面,则人之生也时时劳动,而改造着自然,同时恰亦就发现了人类自己;凡现在之人类和现在之自然,要同为其相关不离递衍下来的历史成果,犹然为一事而非二”,①喀什汉语作家们通过对恶劣环境下的自然生命力的描写,一方面凸显出自然意象对恶劣环境的抗争与超越,对生命的强烈追求状态,进而为读者呈现由生存欲求迸发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通过人与自然的融合在人与物的交替思考中将自然生命意识作为探寻人类生命哲学的一个维度,以求得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类存在意义的探究,实现个体区别于动物的自主生命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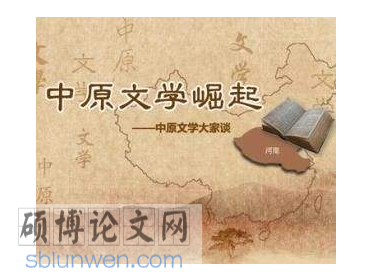
汉语文学论文参考
第二节 历史的挖掘与传承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很多作家善于从历史中发掘爱国主义精神,传递爱国主义的火炬。喀什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喀什汉语作家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创作出很多具有爱国情怀的作品。正如徐梅老师在论文中提到的:“走近历史的深处,去观照那些源头性的事物,从时间的长河中抽取历史事实,从历史文化长廊中撷取那些富有历史感、地域感或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人物来营构厚重深邃的文本。”②喀什汉语作家在对历史进行复原的同时,从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反思当前现实,超越正视历史的基本态度,将创作的主题提升到对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上,展示出个人与国家、民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以史实为依据,把握历史脉搏,观照喀什在古今历史中的变迁,重视历史现象背后的精神底蕴,在理性认知与感性情感的沉淀中,喀什汉语作家自觉承担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职责。
一、历史的深度探求
喀什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多民族集聚的地区,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古城。这种时间上的大跨度和横断面上的多样性,为汉语作家挖掘历史主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新时期以来喀什汉语作家更多地将视野投向与喀什绿洲相关的古今,多民族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便成为了汉语作家写作的重要内容。新时期以来的喀什汉语文学作品中,历史名人、名物的描写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时有出现,不同于以往对民族历史的感知,喀什汉语文学创作在截取重要历史的节点上,把握古代与现代,对历史与民族进行了更多的审视。
喀什汉语作家通过对史料的认真研读,把握喀什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于时间的长河里截取喀什在历朝历代与中原地区的分分合合。新时期以来,无论是史料记载的民族英雄,还是喀什现存的历史遗迹,都是喀什汉语作家从历史角度书写喀什不可或缺的素材。在彰显历史丰富性和厚重感的同时,喀什汉语作家不忘运用文字的形式传递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关于喀什的历史故事最早的就是《穆天子传》了。喀什历史文化学者王时样在《穆王:八骏万里访春山》一文中,作者根据《穆天子传》、《拾遗记》等记载,描述了穆王从周都镐京出发,西渡黄河,进驻新疆,攀登帕米尔。在帕米尔停留之后,穆王来到一个叫“赤乌”(今喀什地区塔县一带)的地方,碰到周朝宗室赤乌氏部落,穆王并娶两位美丽的赤乌氏姑娘为妃,之后穆王又抵达一个叫“曹奴”(今疏勒)的地方,并与曹奴首领互赠礼物,此后穆王南下,沿着“黑水”(今喀什叶尔羌河)上溯,会见了“容成氏”部落,在容成氏部落的帮助下获得大批美玉。关于这段故事是历史实录还是神话故事,一直以来都有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商、周时代,我国西域与中原已经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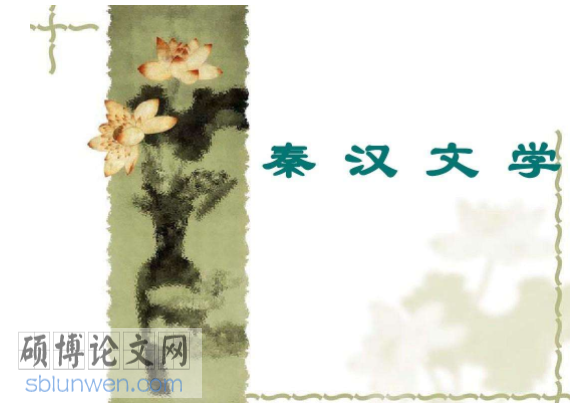
汉语文学论文怎么写
...............................
第三章 崇高美学风格的构成 ............................ 25
第一节 庄严的思想、情感 ........................... 25
第二节 崇高的艺术形象 ............................. 27
第三节 独特的语言风格 ............................. 29
第四章 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未来走向 .............................. 31
第一节 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现状分析 ............................... 31
第二节 喀什汉语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 ......................... 33
结语 ............................ 35
第四章 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未来走向
第一节 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现状分析
喀什汉语创作者生活经历的波折是他们文学灵感的来源和作品情感的归宿,也是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在整个新疆文学资源上,相比于北疆,南疆有更多可供深入挖掘的写作资源,有更多可以展示的美。但是,在现实上,喀什汉语文学创作总体上是逊色于北疆的。良好的文学资源没有产生更多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这些无不和作家自身和外在的因素有很大关系。
首先,在过去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喀什汉语文学创作过度依赖于自然风貌的个体化表述、民俗文化的现象化描写,导致喀什汉语文学作家在长时间的抒写中,难以脱离现有的创作和思维模式,不能够透过这些边地具有历史源流的现象挖掘深度和内涵,也不能够在创作上革新。例如,对自然意象的描写和对风俗现象背后本质的揭示,基本上是一种浅在的阐释,并不能够进行深入的心理层面的展示,缺少对其内涵本质的一种把握、不能够在文学深度上发掘一种应有的厚度。比如对“木卡姆音乐”、“刀郎木卡姆”、舞蹈等风俗的书写侧重点大多数喀什汉语作家都放在了对其源流的探究和价值的肯定,而缺少对其现象的思考和心理情感的展示。换句话说就是喀什汉语作家在表现喀什自然地貌、历史人文等方面难度较小,但在进行深入挖掘内在精神和心理方面难度相对较大。笔者通过相关访谈了解到,很多本土作家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语言上的差异。语言障碍不仅是羁旅作家面临的障碍,同时也是喀什本土作家没有突破的壁垒。虽然本土作家长期居住于此,语言这一媒介终究是不可跨越的障碍。喀什本土汉语作家能够流畅的用维吾尔语言交流的人很少。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导致交流上的障碍,对民俗背后蕴藏的本质也难以把握,从而很难把握人物心理和维吾尔语言的幽默性。喀什汉语作家创作的小说作品,在对过往经历叙述中,也有很多作品反映他们在边地的现实生活,比如朱光华的《新官上任》、肖陈的《翻译苏里坦》、李宏的《一个真心爱鱼的人》和《渡口》、茹军风的《心狱》、蔺高峰《机关兵》、等,虽然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但小说叙事模式过于单一,在心理和情感上显得过于单薄,对作品人物的刻画也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叙事中做客观的描绘,缺少对人物心理的揣摩。因此,对于喀什汉语作家来说,至少是缺少这样一种经历和深刻。笔者在采访喀什相关作家时,也问及创作中的交流问题,但大部分汉语作家都表示语言是阻碍创作的一个因素。例如在采访李成林老师时,他举例说:“主要是语言障碍。比如说我的《新疆好人》就没有那种味道,维语很幽默,但是翻译出来就味道变了。要是能懂点维吾尔语言,我写的会更有意思一点。多掌握一门语言就是多一门技术肯定要好一点。最起码能够抓住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物心理和感情。王蒙当时学习维语,看着墙就说维语的墙,看到椅子就说维语的椅子。主动学习维吾尔语言,通过语言打破交流上的障碍。这些生活中的积累,终于成为他塑造人物形象的基础,把握人物心理的途径,也为他准确的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做好了铺垫。这些无不是王蒙成就的一部分原因所在。”作家杨秀玲也表示语言对写本土小说有一定难度:“还有,一篇好看的短篇小说,语言要精练还要有回味,新疆很多土话特别有意思,简单的一个词能让人物生动而立体。如果你不了解,就很难创作出具有喀什特色的小说和人物。”
........................
结语
新时期以来喀什汉语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在量和质上都有了很大成就。在近四十年的创作中喀什汉语文学创作始终保持着本土性的坚守,保持着对地域特色的不懈追求。这些无不是喀什汉语文学创作发展过程中取得成就,相信随着喀什经济的发展和地位的提升,喀什文学也会逐步的被更多的研究者研究。
虽然在当代文学中较少受到主流关注,但喀什汉语文学创作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从新时期前的少数作家创作,到中青年作家的突起,再到内地作家的参与,喀什汉语文学创作队伍从小变大,从以本土作家为主到多民族、多地域作家的共同创作。在主题方面,喀什汉语作家不断突破旧主题的反复咏唱,从自然意象的冷静观察到现实人生的深入思考,从个人情感的肆意书写到对生命与其意义的探索,从个人价值的实现到民族国家复兴的自我担当,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反思,对人、对自然的洞察等等,都体现出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由主题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在美学风格方面,生存于边塞边缘的绿洲,喀什汉语文学创作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在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关注中,把握其内在的精神特质,在纷繁的社会现实中追求积极、乐观、豪迈、刚毅、崇高的美学风格。总体而言,一方面,虽然喀什汉语作家在理论、修养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喀什汉语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限于各种原因,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的相关文学评论滞后于其创作,不能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指导。总之,喀什汉语文学创作在整体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由于作家情况复杂和个人学术水平有限,文中对创作主体的搜集不免有疏漏之处,得出的相关结论也并非全然无误,本文对新时期喀什汉语文学创作研究是一次新的探索,后来者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在对创作主体分类和主题梳理的基础上,把握其整体美学风格,通过阅读与访谈发现相关问题,提出相关合理化建议,期许我的拙见能够为喀什文学今后的整体发展起到一点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