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涌现出了一批红色经典作品,这批红色经典文学作品高度集中概括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当然还有《小英雄雨来》《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这些红色经典作品不仅成功地书写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代,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安排、文学语言的独特性与表达力、思想内涵的独特性及对读者的启迪性方面成就卓然,自出版以来便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而且获得了国内学界、评论界、舆论传播界的高度关注,多次再版重印,如《红岩》因其超过千万册的发行量至今依然位列当代小说发行量榜榜首。今天探究红色经典作品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出版和传播,对当下我们如何在新时期继承和传播红色革命文化,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精神,出版优质精品图书具有非同寻常的启示意义。
二、来自时代的呼唤——时代精神指引出版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代,时代和社会发展呼唤一种能展现中华儿女在时代浪潮中超越个体局限,实践革命理想的昂扬的精神力量。由此,《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等一大批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的文学作品在此时的产生,成为共和国红色记忆发端期的重要标志。而这些红色经典作品也因其巨大的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在广大基层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批红色经典作品的创作有其时代背景,但它们能够出版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基层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力,与其出版过程中出版人及编辑的“慧眼”“ 匠心”“ 妙手”密不可分。
(一)“慧眼”——主动发掘,出版人的慧眼识珠
发现好的选题与编辑的敏锐洞察力和精准判断力分不开,更考验编辑对时势的把握度。编辑要有一双鹰的眼睛,做慧眼识珠的猎者。敏锐地感受和把握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寻找满足潜在阅读需求的选题。
《红岩》的出版离不开老作家沙汀的推荐,但更与编辑敏锐抓住选题,进一步挖掘分不开。《红岩》就是江晓天从罗广斌等人的一篇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发现的。1958年,江晓天在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有一部罗广斌等三人署名的《禁锢的世界》。他当即写信,很快联系约稿,列入出书计划。
另一部《创业史》则是由于编辑的慧眼,早早收入出版社囊中。1958年,柳青刚下乡采写,当时《创业史》第三稿还没写完,江晓天就料定柳青假以时日必有鸿篇巨制,即派文学编辑黄伊专程前往约稿,约定不论什么时候完稿,不论成稿多少字数。两年后,《创业史》第一部出版。
同样,《红旗谱》能够顺利出版,与作家孙犁的肯定和编辑萧也牧的慧眼识珠也分不开。1956年,梁斌信心十足地把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萧也牧和张羽在仔细阅读之后,发现作品描写革命斗争的主题很好,既符合对新中国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出版宗旨,而小说中的传奇色彩又能够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阅读兴趣,当即签订合同。
(二)匠心——编辑与作者群策群力的倾力打造
好的选题和优秀的作者是优质图书作品成功的一半,但光选题好还远远不够,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出版后的版本大体上是一个作家将编辑、评论家,甚至是读者的意见逐渐融入作品,不断完善修改的过程。可以这么说,“三红一创”红色经典作品在出版时都曾经面临过被编辑们要求修改或“外审”的要求①。
《红岩》原名《禁锢的世界》,成稿时被出版社编辑认为写得过于血腥、基调低沉,建议将狱中革命者的斗争写得再主动些,将原先的“暴露敌人”为主改为“歌颂先烈”为主。《红岩》从创作到定稿,历时3年,经过5次大的修改,终于在1961年底正式出版。
《红旗谱》编辑张羽曾以中青社第二编辑室的名义给梁斌写了一封1500字的长信。“意见”和长信在肯定《红旗谱》的优点之后,认为稿件本身的艺术质量却还远未达到一部红色经典的出版要求。张羽从“第一读者”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如内容剪裁不够,有些地方重复,有些人物性格特征需要加强;思想内容方面主要是对党的领导描写需要加强,要写出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写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②之后,梁斌在张羽和萧也牧的鼓励之下,再次回到河北去拜访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红旗谱》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细致的重大修改。杨沫对《青春之歌》的修改从小说出版前一直持续到小说出版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改写幅度之大是“红色经典”中罕见的。小说出版前杨沫主要是根据审稿意见进行反复修改,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后杨沫综合读者、评论家等各方面的意见对小说文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改,1960年呈现出的再版本是改写幅度最大的一次,1978年的重印版仍然在少数地方进行了修改。
(三)妙手——编辑妙笔生花
一本书的成功,背后有着编辑无数的心血,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是策划者、组织者,甚至还可能是参与编写者——删改文章,或重新架构,或改写。
1956年,作者曲波抱着刚刚完成的40万字小说《林海雪原荡匪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以为会被出版社退稿,没想到20天后得到的是作品很好可以发表的消息。出版社审稿编辑龙世辉通知曲波:“我们确定要出版你的小说,但需要做一些修改。原稿小说在语言结构上存在不少问题,文学性不强,严格地讲只是一堆素材”。在出版社的帮助下,曲波完成了稿子修改。之后编辑龙世辉用了近4个月的时间,废寝忘食地整理、誊写、修改,一字一字从写在废纸上的原稿誊写,一句一句整理30万字,书名最后确定为《林海雪原》。
《保卫延安》原来是某丛书编辑部的退稿,作者杜鹏程心不甘,就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雪峰。雪峰亲自审读完书稿后,对书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需要整修。经过作者与编辑的共同努力,书稿从70万字精简为40多万字,才成为后来出版的样子。
中青社编辑《红旗谱》与编辑《红岩》《红日》情况都有所不同。《红日》交稿后未做大的改动,《红岩》的修改近乎重写,其中编辑所起作用非常大,责编张羽所写文字有数万字之多,是作者住在出版社以流水线方式与编辑一起修改的。《红旗谱》的成功萧也牧当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三、出版影响时代精神的传播
文学作品的阅读、接受、改编与流通是其意义生产与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经典作品所承载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它必须通过广泛的传播才能得以实现。反之,“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一批红色经典作品在特定历史时期及之后获得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它所承担的弘扬时代精神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任务。通过对作品出版、发行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这一批红色文艺作品在当时的流通状况与普及程度。
传播学认为,“传播者信息传递与受传者信息接受,是始端和终端的两极,它们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大多数红色经典作品都有类似的传播路径,即报刊宣传、官方认可、座谈会、读者来信、评论家评论等形式,达到连接终端受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
(一)报刊连载、选载宣传
实现从口头文学到书面小说。即正式出版前,小说已为大众所熟悉,如《红岩》在出版前,几百场口头报告演讲和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署名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在《红岩》接受和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形成并巩固了读者心目中“真人真事”的印象,形成对《红岩》作者的信赖。同时,由于《红岩》属重大题材,是中青社重点图书,出版社动用所有资源,以最高调、最大力度向社会推介这部新作,包括在报刊连载或选载、在媒体发书讯、召集座谈会、组织著名评论家撰写评论文章等。选载、连载的报刊有共青团中央直接管控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还有《中国少年报》以及《延河》等。
《红旗谱》第二部《播火记》在正式成书之前,《播火记》分别于1958年、1960 年、1961年在《蜜蜂》《新港》《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北京晚报》和《黑龙江日报》连载或选载,第三部《战寇图》(即《烽烟图》)于1959年、1962年分别在《新港》和《河北文学》选载。仅在1958年一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大报和《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天津日报》《辽宁日报》《杭州日报》《西安日报》《哈尔滨日报》《新民晚报》等地方报纸,以及《中国青年》《文学青年》《北京文艺》《上海文艺》《蜜蜂》《萌芽》等刊物,纷纷发表书讯、书评或访谈,可谓全国性地毯式的宣传攻势。
《创业史》两部的出版都是先在期刊连载,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点推出。《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是1959年4月在《延河》4月号至11月号连载(其间在8月号小说题名改为《创业史》),1959年11月在《收获》第6期全文刊载。此次刊载极大地增强了《创业史》在文坛的影响力。⑤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可以说,在正式出版前近一年的报刊连载,大大增强了《创业史》的影响力,一出版立即供不应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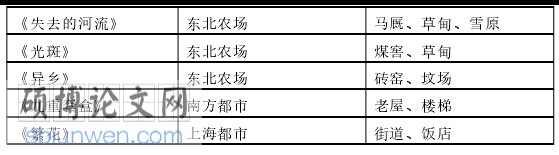
文学期刊论文怎么写
(二)官方认可
1960年,《创业史》出版后不久即在第三次文代会上被多位领导在报告中作为典范大力表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中两次提及《创业史》,将《创业史》与已经成为经典的《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林海雪原》等作品并列,称赞“《创业史》深刻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同面貌,塑造了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革命农民梁生宝的真实形象”⑥。茅盾也在报告中多次赞扬《创业史》,指出“人物塑造的方法是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的”⑦。
同样,当时国内文艺界最权威的人物周扬、郭沫若和茅盾对《红旗谱》给予明确肯定、高度评价。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做的报告中用大段篇幅褒扬《红旗谱》。郭沫若亲笔为《红旗谱》《播火记》题写书名,茅盾当着田间等人的面亲口对梁斌说“《红旗谱》是里程碑的作品,《播火记》也是里程碑的作品”。
(三)座谈会
出版社联动作协、期刊社、大学等机构组织座谈会,座谈会有普通读者参加学习的,也有专业性的文学批评座谈会。如1960年7月作协西安分会召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郑伯奇、杜鹏程、王汶石等作家和西北大学文学评论组、报刊编辑等。1960年9月,中共长安县委宣传部、《延河》编辑部召开座谈会,会议发言记录《座谈〈创业史〉第一部》在《延河》11月号发表,随后《人民日报》1960年11月16日以《长安人谈〈创业史〉》为标题转载。《光明日报》1960年7月24日刊登《西安地区的作家和青年作者座谈柳青的〈创业史〉》,北京大学中文系也举行了关于梁生宝形象的学术研讨会。
1958年2月26日《文艺报》(当时全国最高、最权威的文学刊物)在中国文联大楼举行《红旗谱》座谈会,请来梁斌的老同学或老战友、《红旗谱》所写当年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或领导者座谈。大家一致对小说给予高度评价。座谈记录摘要发表于《文艺报》1958年第5期。同一期的《文艺报》还发表评论家方明的文章《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读小说〈红旗谱〉》。
(四)文学评论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传播,其主要原因在于用大量的历史细节,真实、鲜活体现了时代精神风貌,因此获得了具有舆论领袖地位的文学批评期刊以及相关舆论精英的高度关注,并逐渐影响到传播受众的终端——普通读者。具有一定分量的杂志,如《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在当时的态度对全国具有示范、引领和导向作用。
《红岩》的书评包括专家评论与读者来信。责任编辑张羽化名张念苓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62年1月13日的《冬夜围炉话〈红岩〉》是第一篇评论文章。整个1962年,相关评论文章确可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从国家最权威的《人民日报》《文艺报》,到各省级、地级报纸,都开辟专栏或专版发表介绍、评论、读后感。在媒体浪潮推动下,出现全民阅读《红岩》的奇观,各地报纸选载、连载,新华书店读者排队抢购等现象。
第三次文代会之后,全国各大报刊掀起了报道和评论《创业史》的热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文汇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羊城晚报》等纷纷发表关于《创业史》的文章,甚至在全国范围发起了“学习梁生宝”的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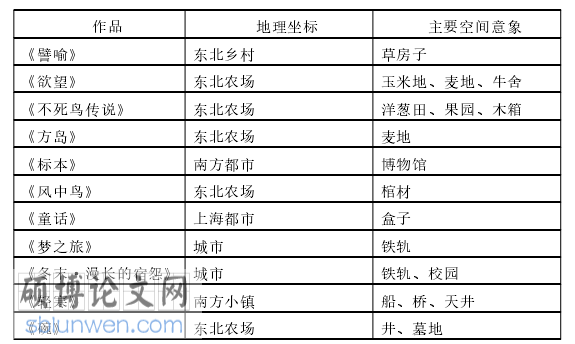
文学期刊论文参考
(五)改编再创作
从传播受众方面,很大一部分民众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接受不是通过对文本的直接阅读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其改编后的电影、戏剧等。“改编”是文学作品扩大接受面、增加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天,以这批红色经典为源头,在国内不断被改编成为舞剧、歌剧、京剧、连环画以及电影、电视剧,影视媒体的传播,再次增加了这些红色经典作品的感染力,并获得不同国家以及地区读者的共鸣。如《红旗谱》出版后,曾先后被北京评剧团改编为评剧,被承德地区京剧团改编为京剧,被河北省话剧院改编为话剧,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天津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故事片。
四、结语
出版受时代精神的指引,也影响着时代精神的传播。无论社会进步和时代如何发展,优秀的出版物都离不开图书出版过程中出版人和编辑的“慧眼”“ 匠心” “妙手”,以及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主动作为、传播媒介的集约效应和受众者的情感共鸣等。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