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法学论文,笔者认为个人医疗信息作为一种的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性质的重要人格权,对医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人工智能载体处理个人医疗信息更有助于发挥其最大价值。
第一章人工智能载体侵害个人医疗信息现状分析
第一节人工智能载体侵害个人医疗信息实践分析
一、人工智能载体侵害医疗信息原因复杂
人工智能载体在医疗领域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其掌握大规模个人医疗信息数据,因此人工智能载体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极易发生侵害个人医疗信息的事件。人工智能载体侵害个人医疗信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的行为导致人工智能载体侵害个人医疗信息;二是人工智能载体自身造成侵权。
人工智能载体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应用都需要人类的参与,因此第一个原因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人工智能载体存在技术上的漏洞或者瑕疵以及人工智能载体信息处理者后期对人工智能载体的操作过程中出现错误行为。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载体不同,前者是根据特定算法运行的计算机系统;而后者则是前者以及由前者控制的各种硬件设备的结合体,如安装人工智能系统的电脑设备、机器人等。因此人工智能载体存在技术上的漏洞主要是指人工智能载体中人工智能系统在设计研发的初期程序和代码上存在的错误,进而导致后期的应用过程中发生个人医疗信息处理不当或者泄露等医疗信息侵权行为;人工智能载体存在瑕疵是指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的硬件设备出现故障,进而人工智能载体侵害个人医疗信息的情形。在上述技术存在漏洞和硬件设备存在瑕疵的情形下,还极易发生黑客攻击盗取个人医疗信息数据进而导致大规模泄露和非法利用的事件,因此涉及的行为主体包括人工智能载体的设计研发者、生产者以及黑客等第三人。人工智能载体的决策和行为除了依赖研发者设计的特定算法外,还依赖信息处理者对人工智能载体的操作行为,当信息处理者在对人工智能载体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出现错误行为时,将会导致人工智能载体不能按照特定算法规定的路径产生医疗信息数据分析、处理结果,并且在此过程中发生医疗信息侵权行为。侵权行为虽然不是由信息处理者直接做出的,但是侵权行为应当归因于信息处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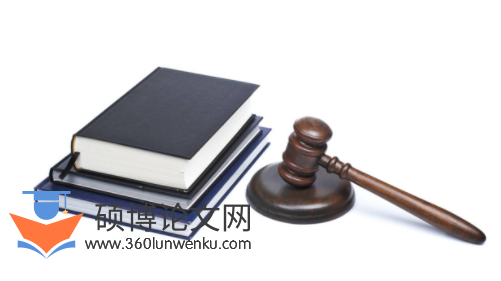
法学论文怎么写
..........................
第二节人工智能载体侵害医疗信息既有法律规定分析
一、既有法律规定中相关概念内涵不明确
本文讨论的“人工智能载体侵害个人医疗健康信息责任”这一主题中,涉及到两个基础概念,分别是“个人医疗信息”以及“人工智能载体”,弄清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以及法律性质是分析侵权责任的基础。
首先是个人医疗信息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内涵。就目前的我国立法情况来看,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均提出了“医疗信息”、“医疗数据”等相似概念,也有一些文件中详细地阐释了概念内涵,如,《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认为个人健康生理信息是指个人因看病就医而产生的一系列记录中所包含的信息,比如病历、住院日志、医生书面嘱托等;25《健康信息学—推动个人健康信息跨国流动的数据保护指南》中认为个人健康数据是已标识或者可标识自然人健康状况的个人数据;26《信息安全技术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指南》中强调个人医疗健康数据的可识别性以及其以电子数据的形式被记录的。27这些相似概念在内涵上有重合之处,但也存在差异,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对上述概念的内涵和范围的看法各不相同,个人医疗信息缺乏明确的法律边界。
其次是“人工智能载体”的内涵尚未形成共识,困境在于“人工智能”的内涵无法形成共识。“人工智能”一词最早出现于1956年,约翰麦卡锡教授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召开的主题为“用机器模仿人类习以及其他方面智能”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并且将人工智能定义为能够表现人类智慧、模仿人类行为的机器。28但是该定义仅仅只是被计算机领域接受,而各个学科对“人工智能”普遍接受或者法学界普遍认可的内涵还尚未形成。当前,我国涉及人工智能的政策法规文本中,很少根据人工智能的本质、特征、特有属性对其进行明确概括说明,大多数文件只是零散地在涉及人工智能的语句中给出特点描述词或者类型归纳词,对于准确阐释人工智能没有帮助。我国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是《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其中规定人工智能指利用计算机或者由其控制的设备,可以感知外部环境、获取新知识、对相关情况进行推理预测,进而具有与人类相似的“智慧”,并且对其进行扩展和延伸,模仿人类行为。29《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中涉及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列明的人工智能技术范围相同,包括机器学习、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生物特征识别、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关键技术。
.......................
第二章人工智能载体处理医疗信息侵权责任认定困境
第一节人工智能载体侵害医疗信息责任主体认定难
一、人工智能载体民事主体地位存在争议
人工智能载体是否可以作为侵害个人医疗信息行为的责任主体,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民事主体地位。各个学者从法律层面出发结合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考虑,对人工智能载体的法律地位形成以下三类观点:客体地位说、中立说地位和主体地位说。
首先是客体地位说,该学说主张人工智能载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民事客体的地位,民法中规定的“物”。客体地位说还可以细分工具说、软件代理说和道德欠缺说。工具说认为人工智能载体属于人类工具,因而不具有民事主体地位;35软件代理说的主张者Susanne Beck认为人工智能载体的核心——人工智能系统属于知识产权的指向的对象,因此人工智能载体是软件代理,为人类服务;36道德欠缺说认为人工智能载体不同于自然人,其不具有道德、羞耻心等因而不具有民事主体地位。37其次是中立地位说,主张人工智能载体既不是法律主体也不是法律客体,只是一种在人类的掌控和监管下运行的中介。38最后是主体地位说,该学说认同人工智能载体具有民事主体地位,将人工智能载体作为代理人或者赋予其电子人格。代理人说的代表学者陈吉栋认为人工智能载体的决策行为类似于代理人根据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做出的行为,因此将人工智能载体看做代理人,392017年《欧盟机器人民事责任法律规则》中提出的非人类代理人是人工智能载体作为代理人的有力支撑;电子人格说在《欧盟机器人民事责任法律规则》提出,与拟制人格类似,通过法律技术给予人工智能载体“身份”——电子人格,由此更好的解决人工智能引发的侵权问题。
........................
第二节人工智能载体侵害医疗信息归责体系不完善
一、医疗信息处理者过错推定原则适用笼统
当前学界关于人工智能载体信息处理者应当按照何种归责归责原则承担侵权责任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分别是信息处理者承担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但是在人工智能载体侵害个人医疗信息的场景下,人工智能载体应用者还具有个人医疗信息处理者的身份,按照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包含在过错责任中,是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确立责任和责任范围的基础的归责原则,但是不要求被侵权人承担证明侵权人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而是将行为人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倒置,要求侵权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对于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工智能载体的信息处理者,无差别地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并没有考虑到人工智能载体的信息处理者在性质、处理个人医疗信息目的、与被侵权人之间关系等方面存在的差别,“一刀切”地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过于笼统,没有平衡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应用人工智能载体处理个人医疗信息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及非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两类。前者是指依法成立,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疾病预防等卫生机构的总称。上述两种利用人工智能载体处理个人医疗信息的主体在处理个人信息社会地位上就存在突出的差别。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获取、处理个人信息往往是为了疾病诊断、治疗、传染病防治等非营利性、公益性的目的,因此在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获取、处理医疗信息理所当然,没有相关医疗信息无法开展后续工作,其社会地位较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更高;其次,二者在专业程度上也存在差别,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大都是具有医学、药学等相关专业背景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相关就业人员的学历要求逐步提高,即使是三四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也需要博士学历,因此对人工智能载体处理个医疗信息的方式的合理性、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后续的影响都有极强的专业判断。
...........................
第三章人工智能载体侵害医疗信息责任认定规则完善.........25
第一节明确人工智能载体侵害医疗信息的责任主体........25
一、否定人工智能载体的民事主体地位...............25
二、系统设计者脱离生产者单独承担产品责任.........26
三、明确医疗信息处理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27
结语..........39
第三章人工智能载体侵害医疗信息责任认定规则完善
第一节明确人工智能载体侵害医疗信息的责任主体
一、否定人工智能载体的民事主体地位

法学论文参考
根据我国相关民事法律规范,我国的民事法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所以存在“民事法律主体”的概念,是为了确定个体可以在民事法律活动中,能够以自己的行为独立地行使权利、承担义务,更好地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主体的独立地位要求民事主体具备自由意志,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思表示成立或者变更民事法律关系,并且能够以自己的行为独立承担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因此要讨论人工智能载体是否具有民事主体地位的核心在于确定人工智能的分析和决策行为是否出于其自由意志,同时还需要考虑人工智能是否可以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据此,笔者对于人工智能载体的民事主体地位持相对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基于目前人工智能载体的发展水平,其自由意志水平不能和人类的自由意志相提并论,但也存在着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后赋予其法律主体资格的可能性,正如希尔勒教授所说:人工智能在达到必要的条件后,就能具备和人类比肩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作为被人类利用的人工具。
首先,当前阶段人工智能载体虽然具备一定的思维能力,能够根据周边环境和事情进展,运用人类的思维方式,作出符合逻辑和社会价值理念的决策,但是其思维能力是有限度的,尚且不能灵活地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无法与人类相提并论。人工智能载体技术核心在于人工智能系统,其相当于人类的大脑,系统算法是研发人员进行编写,其对医疗信息处理所要达到的效果并不是要求人工智能按照研究人员的想法做出相应行为,而是允许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学习等,自主做出相应的诊疗方案、疾病诊断或者疾病预测等,即研究人员输入的算法只是教会人工智能载体如何运行、按照何种规则处理,也就是说算法使得人工智能载体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分析以及自主决策的能力。但是归根结底来说,人工智能载体目前所做出的自主行为还是依赖人类提供的医疗健康数据和医疗学习模型,仅仅可以模仿医护人员的思维和行为,缺乏感知和情感的内在体验,无法像人类一样在每一次处理医疗信息的过程中进行思考、积累经验,也就是说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载体不具有和人类同样的自由意志。
...............................
结语
个人医疗信息作为一种的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性质的重要人格权,对医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人工智能载体处理个人医疗信息更有助于发挥其最大价值。在医疗行业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普遍使用的当下,个人医疗信息在发挥其公益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被侵犯的风险,面对个人信息权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既不能为了保障个体利益而放弃医疗数据行业的发展,也更不能为了社会利益而放弃对个体利益的保护。通过对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数据保护以及侵权责任相关法律进行分析,对比美国、欧盟等较早关注个人信息保护的国家和地区对个人医疗信息的侵权救济机制,笔者否定了当前人工智能载体的责任主体地位,明确了人工智能载体处理个人医疗信息侵权责任主体的范围,以及上述主体根据其性质、地位的不同使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明确人工智能载体侵害医疗信息责任构成要件判断标准,帮助更好地认定侵权责任,使得个人能够在侵权行为发生后能够得到有效救济,同时也给相关主体警示,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侵权行为发生,从而平衡好医疗信息安全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进步。较为遗憾的是,由于笔者自身的法学理论修养不够以及无法通过实践经历考证医疗行业具体情况,文章无法将问题做到详尽论述,只能结合已经公布在网络中的相关案例以及社会事件进行探讨,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希望自己能在之后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为人工智能载体处理个人医疗信息的保护问题提出更多的解决建议。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