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刘震云小说的欲望书写运用了相当有效的叙事策略:为了体现欲望的普遍性,刘震云以平视普通人物的叙事立场来观察人物的心灵世界;为了突出欲望的顽固性,他精心建构复杂多变的故事空间来强化人物的心理冲突;为了揭示欲望的层次性,他擅长借助精巧圆融的叙事结构来透视人物的精神症结。
第一章刘震云欲望书写的心理成因
第一节现代文学观念的传承
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观念迎来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不仅在于“睁眼看世界”学习了外国的写作技巧,更在于“由内观自身”重新审视了文学创作的理念。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曾经说过“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人权为重”。[2]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认识到文学中呼唤人性的重要性,由此开辟出文学书写的新方向。当论及“人的文学”,势必无法绕开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3]周作人严厉抨击了程朱理学影响下对于人性的漠视,呼吁学界关注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广大知识分子从而走出书房,真正直面人的需求和生活状态,关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作为运用白话文写作的先驱,他在自身的写作实践中切实落实了“人学”的相关理念,极大重塑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促使鲁迅贯彻人道主义理念的是他对“救亡图存”一以贯之的追求,他希望通过审视人的本性来唤醒麻木的人民,实现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这一时期的鲁迅曾经写下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1]从字里行间的踟蹰可以看出鲁迅本人作为“启蒙者”的身份认同与使命担当。事实上,五四时期恰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蓬勃发展的时期。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作家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转型中应该承担唤醒民众的责任,这也使得他们拿起笔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种发自内心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也同样在刘震云身上体现。恰如摩罗所说“刘震云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一位鲁迅式的痛苦者和批判者”。[2]他由于责任而痛苦,因为痛苦而创作,从而直白剖析人性中的各种欲望,讥讽当代社会中物欲横流的种种弊端,履行了身为知识分子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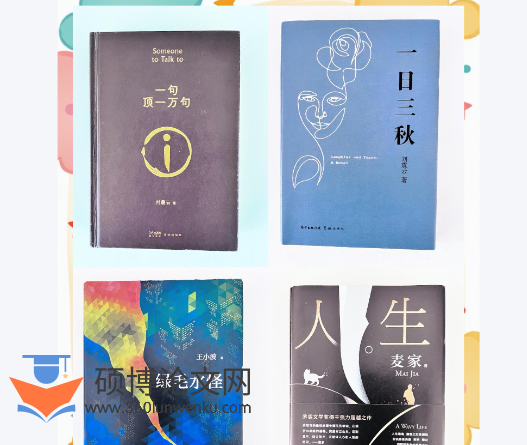
文学论文怎么写
.......................
第二节当代文化思潮的冲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促使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各种消费的刺激之下,人们对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欲望也在迅速膨胀。这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土壤,使其在这段时期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了影响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和上层阶级的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更加贴合普罗大众,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审美天然带有着民间通俗化、娱乐化的特点,更加便于广泛传播与普及。而大众文化在交流传播的过程中因为自带的消费属性,常常与现代思潮中的消费主义文化交织在一起。就像约翰·费斯克(John Fisk)在《解读大众文化》中所认为的,“大众”指的是相对没有社会权力的群体,他们也被称为消费者,不但拥有自己的文化形式及兴趣,还经常与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对立甚至相互抵抗。所以,一件商品的流行就必须要满足大众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1]在这样的消费主义语境中,商品价值成为了衡量事物好坏的唯一标准,只要能够彰显商品价值并从中获利,即使是颠覆传统也势在必行。所以,在这样解构传统的躁动时代进行文学创作,必然会受到拜物教“唯利”思想的影响。“文化工业的典型文化本质不仅仅是商品,它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商品”。[2]国内的《钟山》杂志就曾在八十年代举办一期“新写实小说的大联展”,在文学期刊的运营营销方向进行了调整,主动选择接受商业运作模式的渗透。这种文学创作和商业价值融合的创作导向,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
..................
第二章刘震云小说欲望书写的基本主题
第一节物欲对情感的侵蚀:沉沦与异化
余华曾经说过:“我更关心的是人物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2]从欲望出发,能够更全面地审视生而为人存在于人世间的价值感。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论及“人的存在”时提出了著名的“需求理论”,他将人的需求一共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级,而“物质欲望”就属于最基础的生存欲望,吃饱穿暖也是人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逐渐膨胀,不再满足于基础欲望,在对锦衣华服的向往之中,逐渐迷失了心灵的方向,陷入物欲的泥沼,沦为消费社会光怪陆离的一份子。
刘震云的“官场小说”深入勾勒了官场中各色人物,对其在复杂的人际网络影响下微妙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深刻表现出人们为了物质生活而挣扎沉沦的样子。《单位》中刚刚大学毕业的小林仍保持着理想主义的天真,对单位中的蝇营狗苟不屑一顾,一心只想要按照自己的性情行事。而他在和单位中其他同事的交往中依然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的想法,甚至面对前辈也不留情面,颇为我行我素。但是现实的压力很快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带来的后果:同事关系紧张导致他迟迟不能入党,更别提升职务,而在官场环境中物质生活的苦乐恰恰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以住房需求为例,小林因为级别低只能与人合住,“一次冲突起来,就开始互相不容忍,相互见面就气鼓鼓的。最后弄得四个人一回去就不愉快,吃饭不愉快,睡觉也不愉快,渐渐生理失调,大家神经更加不耐烦。隔三差五,总要由不起眼的小事发生一场或明或暗的冲突。”
........................................
第二节权欲对精神的扭曲:妥协与屈从
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1]“权力”这个古老而又迷人的词汇跨越古今中外,贯穿历史的长河闪耀至今,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解读研究。亨利·列斐伏尔曾在《空间的生产》中将权力引入了空间的场域之中,他认为“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全是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2]揆诸刘震云的作品,我们不难在各种变换的空间场域之中探寻到权力的踪迹,甚至仔细研究之后会发现,错综复杂的故事背后真正的主导力量就是权力,而看似形色各异的人物也宛如提线木偶一般被权力欲望所操控着,构成一个复杂的权力场。
一、家庭中的权力
“家庭”是最基础最常见的社会空间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刘震云在早期写作时就已经关注。于一九八八年创作的《爹有病》就聚焦在一个父亲生病的小家庭中,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审视家庭成员间存在的权力场。文章一开篇身为弟弟的“我”和哥哥去庙里抢香灰给生病的父亲吃,一路上兄长屡次教训“我”不应该在父亲生病时关注其他。“胡说!爹在家病成那个样子,你却想吃羊肉烩面!”“哥却开始责备我,说这时候不应该想姑娘”。[3]刘震云用极其简单但却荒诞的情节勾勒出被父权控制下的一家:暴力专制的父亲、言听计从的母亲和相互压制的兄弟。马斯克·韦伯曾经说过:“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4]本文中的父亲就是如此,他为了治病,不顾我的反对强行掐死了“我”的兔子,还将“我”绑在荒野上,仅仅因为“我”命硬克爹。正如本文的主人公“我”亲口所说,“我病了,看不看,我决定不了,爹说不要看,就不看了。爹病了,却要倾家荡产。”[5]可以说,在父权的面前,“我”作为儿子是丝毫没有发言权,一直处于下位失权的状态之中。
.................................
第三章刘震云小说欲望书写的叙事策略...............................32
第一节欲望的普遍性:平视的叙事立场.............................32
第二节欲望的顽固性:多变的故事空间.............................34
第三节欲望的层次性:圆融的叙事结构.............................37
第四章刘震云小说欲望书写的多重意义...............................40
第一节生命意识的张扬...........................................40
第二节幽默风格的彰显...........................................42
第三节人文精神的回归...........................................44
结语....................................47
第四章刘震云小说欲望书写的多重意义
第一节生命意识的张扬
人类生存的意义在何处,这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学者们思索的问题,从古至今人们都渴望得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在音乐、美术、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相关表达,作家们也试图通过文学作品给出回答,就在对其不断追问的过程中,生命意识油然产生。想要分析生命意识,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到问题本身,也就是如何看待人的生命。在中国古代先秦哲学中,不论是儒家学派的孔子和孟子亦或是道家学派的老子等,均表达过对“人”生养于天地之间的理解。总体来看可以简单理解为“仁”与“礼”二字,“仁”将人类的个体彼此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社会群体,而“礼”将群体进一步划分成为阶层,又将人类区分开来。在中国哲学的体系中,人类生存的价值始终处于群体环境之中,通过和其他人之间彼此联系从而锚定生命的位置,获取人生的价值。但在西方哲学中,生命的意义在于对自由的执着追求。萨特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质,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造就其本身,“事实上我们就是那选择的自由,而不是我们选择了自由。我们是被判决为自由的,像前面所说,或者海德格尔所说的是‘被抛入的’”。[1]到了二十世纪初,西方盛行生命哲学理论教导人民对生存环境的残酷进行深入的认知,同时改善自身去适应和改造世界,认为恰恰是生命本身组成了世界,对于改造世界具有极大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特点在刘震云的作品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在谈及作者的创作动机时,刘震云曾表示“作者要表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缝隙透出来的一丝冷风、一丝暖意、一丝生活的味道,这些说不清的东西,就是作者要说清楚的”。[1]他在表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缝隙”过程中,选取了人们最常见的生存状态进行加工,致力于探索生命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复杂的关系,思考并揭示生命内部矛盾变化的过程。这样的创作动机不仅凝集了作者对生命的独特思考,也丰富了新世纪作家们对于生命意识的态度。刘震云试图在日常的生活中挖掘出细微而又真实的欲望,从中管中窥豹引导读者反思生命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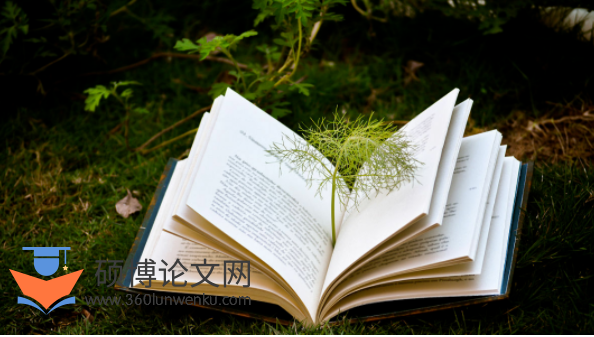
文学论文参考
.............................
结语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刘震云以“新写实小说”创作而蜚声文坛,虽然他创作的不少作品带有“新写实小说”的共性特征,然而,评论界概括的“新写实小说”的一般特点并不能完全涵盖刘震云小说创作的全部艺术特征。综观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实践,其作品中反复呈现却又很少被当代研究者所论析的“欲望书写”这一特色应当引起当代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本文通过仔细梳理和深入分析,发现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塔铺》《手机》《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诸多小说均涉及“欲望书写”现象。总的来说,刘震云的小说高度关注人的物欲、情欲和表达欲,他常常借助独特的故事叙述,来揭示人物情感世界遭受物欲侵蚀之后所表现出的沉沦和异化,或展示人物精神意识在权欲的扭曲下所导致的妥协与屈从,或摹写人物受到表达欲之驱动而流露出的对于孤独的回避以及对友情爱情的渴求。值得注意的是,在欲望书写的过程中,刘震云的小说采取了平视的叙事立场,建构了多变的故事空间,并且设计了圆融的叙事结构,以呈现人物欲望的普遍性、顽固性和层次性,事实证明,这样的叙事策略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