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知青小说中的爱情叙事映射出时代变迁下知识青年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体验。通过对不同的爱情类型进行研究,能够深入洞察知识青年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思想状态和情感波澜,同时也能透视出时代变迁下社会的风貌及人的生存境遇。
1绪论
1.1解题本文以1978-1984年的知青小说为研究对象,以三种不同类型的爱情为切入点,分析这一阶段知青小说中的爱情叙事特点。
关于知青小说的阶段划分,本文采用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的划分标准。杨健将知青文学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知青文学(1953—1966年),第二阶段为“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1969—1978年),第三阶段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1978—1989年),第四阶段为后新时期的知青文学(1990—2000年)。其中,新时期知青文学又细分为前期(1978—1984年)和后期(1985—1988年)两个阶段。本文选取1978——1984年的知青小说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1978年前的知青文学大部分并未做到真实展现知识青年的生活情状,一方面,知识青年作家们多是借文学响应号召进行政治宣传,宣扬“知青运动”。如《岔河村的姑娘们》,其内容充满了政策内容及政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那些隐匿于地下对自我进行深度剖析的作品,则在清查中被销毁。如《北大荒风云录》中,王大闻清楚地记得“连队对思想政治工作抓得挺严,要是有本什么书都藏着掖着,相互保密”①。他曾带回《一只绣花鞋》和《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在连队里讲述,被发现后,全连迅速召开批评大会,要求他一遍遍地写检讨并接受批评②。再如,赵金星1968年写有《哲学的批判》,1969年便因《哲学的批判》一文和“破坏上山下乡”而入狱。因此1978年前值得研究的作品甚少。
第二,在1984年后,知识青年作家的笔下开始有意识的消除“知青经验”,使得“知青文学逐渐成为开放性的题材”③,知青文学逐渐和“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等发生深度融合,而失去了自身的独特视角。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1979-1984年期间,知识青年群体经历了返城、待业、就业和回归正常生活的艰苦历程,他们此前被禁锢的思想也在政策的落实下得到解放。一方面,知识青年以强烈的参与感,对下乡生活进行再现,揭示真实且细致的心理活动,控诉历史伤痛,展现一代人的命运和心理历程。另一方面,知识青年作家经过前几年的反思,开始发生转变,将目光逐渐投向现实生活,丰富了知青小说的创作主题,初步展露了知青小说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
1.2相关概念梳理
第一,知青文学。知青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成为了文学的中心,代表着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变化。学界对知青文学的界定众说纷纭,基本围绕创作者身份和题材内容这两方面进行划定。本文沿用洪子诚对知青文学的定义:“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主要内容,主要是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如返城后的情况”①。知青文学中的知识青年特指于学校毕业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下放到乡村、兵团的青年人。定宜庄对知识青年的概念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知识青年指“所有未能继续升学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青年”,包括“回乡知青”和“下乡知青”。而狭义的知识青年则限定为“1962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②。本文所采用的概念为狭义知识青年,正是以“外乡人”身份进入乡村、兵团的下乡知识青年们,才能对那段漫长的岁月,有着更为丰富的感受与情感体验。
第二,知青小说。依据洪子诚对知青文学的定义,知青小说是指具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作家创作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涵盖了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活经历,同时也包括了他们返城后的生活状况。
第三,爱情。爱情与文学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文学的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大量歌颂爱情的作品。古往今来,思想家、哲学家等对爱情的定义十分丰富,本文所采用的概念是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对爱情的定义,即爱情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使人们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综合的(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互相倾慕和交往之情”③。这一概念既明确指出了爱情的生理本能基础,也提出爱情的社会属性。此外,由于知识青年下乡时期的特殊语境和复杂现实,本文也将一部分书写婚姻生活的作品纳入了研究范畴之内。
......................
2知识青年之间的爱情
2.1血统论对爱情的影响
血统论观念自古有之,其具体内涵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中指出:“族但举血统有关系之人,统称为族而”①。苗威进一步阐释:“所谓血统,即‘拥有同一血脉系统’,或者是‘同一祖先的血缘系统’……‘血统论’是以血统为核心判定,无限地提高甚至绝对地对民族属性程度进行阐述的学术理论”②。这表明传统血统论主要服务于宗族社会和民族认同的建构需求。在十年文革期间,血统论发生了异变,具体表现为,以父辈的身份和成分来决定子女的前途命运与政治发展。当时,阶级成分成为划分人群的标尺,将人们划分为红三类——工、农、干部子女,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知识青年自小便饱受此思想之苦,因父辈的成分而遭到定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口号。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为社会和他人所否定,沦为社会底层,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在描绘知识青年之间的爱情时,1978-1984年间的知青小说揭示出血统论对知识青年爱情的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导致了知识青年情感的异化;其二,让知识青年的爱情救赎带有虚妄色彩。作者在揭示血统论对知识青年的这种影响时,往往跳出叙述的层面进行叙事干预。
.......................
2.2矛盾而复杂的人性
在知识青年之间的爱情中,1978-1984年间的知青小说还揭示出了知识青年矛盾而复杂的人性。作品深刻揭示了知识青年身上坚韧与懦弱并存的特质,真实地呈现出他们在渴望精神共鸣与追求物质享受之间的二重性。为了全面展现知识青年人性的复杂性,作者在叙事策略上既采用全知视角,让读者得以洞察人物内心世界,又巧妙运用三角恋叙事模式,通过人物关系的多重纠葛,使人物形象更显立体饱满。
2.2.1坚韧与懦弱
下乡生活对于知识青年来说是痛苦的,但是面对这份痛苦,知识青年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部分知识青年在面对苦难时,展现出坚忍不拔的态度,相互扶持,将爱情转化为支撑彼此生存的力量,彰显了人性的坚韧。部分知识青年在携手面对苦难时,则暴露了人性中的懦弱,选择了向苦难妥协,甚至走向了自我毁灭。第一,逆境中的知识青年们展现出非凡的坚韧,凸显了人性的光辉。尽管生活给予他们严酷的考验与诸多不公,使他们的心灵一度被绝望的阴霾所笼罩,但多数知识青年凭借爱情的力量,迸发出了超乎寻常的韧性。他们不仅战胜了重重苦难,重新燃起了拥抱生活的勇气,甚至开始追寻并实现曾经的人生理想。
叶辛在《蹉跎岁月》中塑造的柯碧舟,因出身问题在公社中备受排挤。无论是集体户内的知识青年还是湖边寨的村民,都与他保持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在湖边寨的日子里,柯碧舟对未来感到迷茫,甚至走上了自杀的绝路。然而,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回乡知识青年邵玉蓉的出现犹如一束光,照亮了柯碧舟黑暗的人生。她的温柔、善良和坚韧不仅拯救了柯碧舟的生命,更抚慰了他的灵魂。当柯碧舟为救牛不慎摔下悬崖导致骨折时,邵玉蓉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照顾他的重任。她为他精心熬制鱼汤、缝补衣物,用无尽的温柔拂去了他内心的伤痛,告诉他社员们并未因他的出身而对他有所轻视。这份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柯碧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抛弃此前所表现出的懦弱,决心用自己的力量为山寨做出贡献。在发现湖边寨、暗流大队等地尚未通电后,柯碧舟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造电事业。
...........................
3知识青年与村民之间的爱情..................................31
3.1拯救者............................................31
3.1.1落后贫瘠的乡村形象................................31
3.1.2女性农民的生存困境.......................33
4知识青年与市民之间的爱情..........................45
4.1三种爱情目的.............................................45
4.1.1用爱情解决生活困境..................................45
4.1.2将爱情作为心灵之旅....................................47
5透过爱情类型看知识青年的悲剧............................60
5.1理想的幻灭.......................................60
5.2乌托邦式的乡村记忆.............................62
5透过爱情类型看知识青年的悲剧
5.1理想的幻灭
这一时期的知青小说中,在知识青年与村民之间的爱情故事往往可以得见知识青年理想幻灭为核心的悲剧主题。知识青年一代,在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对于六七十年代的知青来说,英雄主义曾经是哺育他们成长的摇篮,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滋养。”②这些青年深受革命先烈精神的鼓舞,怀着成为英雄的崇高理想,怀着满腔热忱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他们信心满怀地奔赴乡村或生产建设兵团,期待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实现人生抱负,开创一番事业。然而,现实的乡村生活很快消磨了他们的自信与激情。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他们的理想难以实现,精神世界也随之崩塌。理想破灭这一知识青年最珍视、最执着的追求落空,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巨大打击。分析这种理想幻灭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两方而:其一,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二,知识青年自身对乡村及其文化的认知偏差与心理排斥。
第一,外部社会环境影响下的理想幻灭。在《蹉跎岁月》中,作者叶辛借杜见春之口,生动地描绘了知识青年下乡时的勃勃斗志:“我是积极主动地要求下乡来的。你想想,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风气运用,如海的红旗,欢送的人流,充满期盼的笑脸,改造世界、建设祖国的崇高职责,一代革命青年,能无动于衷吗?能站在时代的潮流之外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一定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用劳动的汗水改造世界观,做时代的开拓者。”①这段话详尽而生动地揭示了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时的澎湃心情,他们立志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实现建设的理想。但很快,在领略到当时社会环境中所弥散着的错误思想观念的威慑力后,杜见春便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理想,甚至对自我存在的价值都产生了怀疑。杜见春在父亲被打为反动派后,上大学名额被取消,还遭遇了流氓的殴打和大队长的折磨。在身心备受摧残的境遇下,她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质疑自己远离家乡、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难道她远离家乡,毅然放弃留城的条件,投身到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希望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生活?她犯了什么罪?她做过什么坏事?她为什么要遭受如此磨难和非人的生活啊?”②这种“政治上受歧视,思想上受压制,生活上受限制,劳动中受迫害”③的生活,让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她选择了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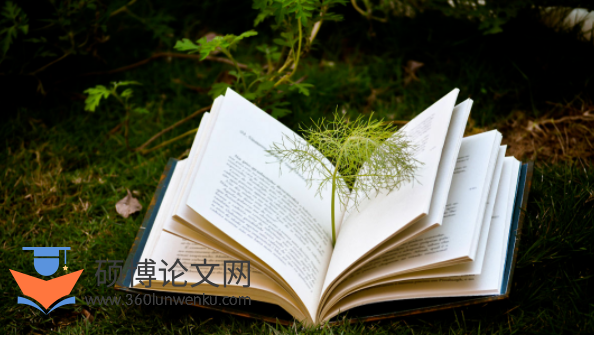
文学论文参考
................................
结语:1978-1984年知青小说爱情叙事的价值与意义
1978-1984年间的知青小说爱情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它不仅突破了“文革文学”在文学形式和主题内容上的局限,还为后续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表达形式和思想资源,正如朱德发所指出“不仅在审美形式上花样翻新,名目别致,而且在审美内容、思想意蕴、人物性格、审美格调诸方面呈现出开放多样的艺术风范,致使情爱文学由‘十七年文学’的单色调向新时期的多色调转换”①。通过对这一时期知青小说爱情叙事的梳理与分析,可以从艺术表达和主题内容两方面总结其价值和意义。
一方面,艺术表达的突破与创新。在文学形式上,这一时期的知青小说爱情叙事打破了“文革文学”因艺术表达单一而导致的雷同化倾向,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叙事视角的多样化。知识青年作家突破了此前关注政治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现实生活和个体情感的微观观照,使文本在叙事视角上变得更为灵活多变。陶东风在研究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叙事角度从传统的全知视角,向限制视角和跳视角的转化。”②这种转化在知识青年与市民的爱情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交替使用,生动展现了知识青年群体对爱情的理解与困惑,突出文本角色的个体叙述者地位,使文本的私性故事与人物主体性得到彰显。如《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两个第一人称视角之间的来回转换、《塔》中五位知识青年的多重视角转换、《飘逝的花头巾》中两个“我”的叙事视角的巧妙转换与处理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家群体的创作实践带来了女性叙事视角的丰富发展,使文本在探索爱情主题的同时,也深化了对女性价值的思考,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和《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第二,心理空间的深入呈现。知识青年作家在描写知识青年返城后的生活时,注重挖掘人物的心理空间,展示他们内心对于爱情的思考和困惑。这种心理书写主要通过两种种艺术手法得以实现:一是运用内心独白直接呈现人物的意识流动,如《本次列车终点》中陈信面对爱情抉择时的矛盾心理;二是通过梦幻与现实的冲突叙事,建构具有象征意味的心理图景,如《在运河边上》以“我”的内心世界中爱情理想与世俗现实的激烈碰撞,深刻揭示了女性在婚恋压力下的主体性坚守。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