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根据郁达夫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以及具体“创伤性情境”,划分出郁达夫几次明显的抑郁发作与轻躁狂发作。但实际上抑郁与躁狂的转换要复杂的多,二者可以混合发作,同时出现,可能几天之内甚至一天之内就可以交替出现,由于学力限制,有些细微的“创伤性情境”并没有展现在本文中。
第一章1913-1921:留日时期精神障碍与文本互动
1.1抑郁发作的病理呈现与社会心理动因
从郁达夫的童年开始到从日本留学归之前来,这一段时间是郁达夫精神障碍的第一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抑郁发作的特点。而抑郁的病因及发病机理有着诸多方面的因素,精神心理研究界普遍认为,生物化学、神经内分泌、遗传因素、心理社会因素会程度不一地促发精神障碍的发生。而对于本研究而言,若想明确郁达夫这一时期抑郁发作的病因,生物化学、神经内分泌,已经不再适用,况且上述因素仍然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心理社会因素在精神障碍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对一些患有抑郁的病人而言,心理社会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是直接导致了抑郁的发生。所以这一节先对郁达夫作出医学诊断,再将视野放置于郁达夫的童年时代和留日的青年时代,从社会心理因素挖掘导致他精神障碍的心理机制。
1.1.1郁达夫抑郁的初现及症候
根据郁达夫精神障碍的整体性把握,有学者认为郁达夫可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郁症),此诊断根据诊断标准大致可信。①一般认为,双相情感障碍是指临床上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的一类的心境障碍。每一病 相均有对应的核心症状,躁狂发作时,表现为情感高涨、兴趣与动力增加或易激惹为主;而抑郁发作时,其往往伴随情绪低落、兴趣减少或缺乏、思维行为迟滞等核心症状。双相障碍往往以抑郁为首次发作,且过去没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所以临床上首诊往往容易误诊,但如果后续有躁狂发作且持续1周以上,根据指征便可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文学论文怎么写
........................
1.2抑郁与文本内外
针对留日时期郁达夫抑郁发作的诊断结果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抑郁病因和诊断切入进作家所处的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以此作为前提,刺探到作品内部。笔者认为抑郁成为了郁达夫独特的艺术气质来源,为郁达夫在留日时期创作的小说集《沉沦》中的颓废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情感色彩。
1.2.1抑郁提供丰富的情感与思想深度
抑郁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和创作天赋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外文化中均有所涉及。柏拉图曾探讨过艺术创作中的“疯癫”,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来到诗歌的殿堂却没有被缪斯的疯癫触及,仍然相信仅仅依靠技术就足以使他成为出色的诗人,那么他和他清醒时候的创作将永远无法达到完美,与那些受到启示的疯癫者相比,将会显得黯然失色。”①而中国也有相近的观点,韩愈提出的“气盛言宜”的创作主张,即体现了作家精神力量对创作的影响。
在弄清抑郁是如何为郁达夫提供气质来源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郁达夫忧郁、敏感的性格与他选择走向文学创作之路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有数据显示,作家群体患有精神障碍——包括精神分裂、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率要比普通人群的发病率高出两三倍。诗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13倍,他们的自杀率也最高,高达18%。②这组数据或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情感丰富或者情感极端的人更容易选择和艺术有关的职业,也就是说,作家在进入到文学创作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患有精神障碍上表现出一种可能性。而郁达夫在正式进入小说创作之前,就已经有过抑郁发作的情况,甚至在更早之前的童年时期就表现出极其敏感、多疑又自卑的性格。在1913年到1922年间,是郁达夫精神转为病态,抑郁发作最为严重的时期。此时,诗词是郁达夫最先创作的体裁,诗词创作最为活跃,创作数量也最多,达300余首。其中日本风土人情诗、爱情诗、自述诗最多。其诗歌风格也与郁达夫抑郁发作的情感特征相辅相成,具有感伤的特点,并呈现出浓烈的哀愁。直到1920年从《银灰色的死》开始,具有颓废风格的小说才逐渐成为主要的创作体裁。
.........................
第二章1921-1933:躁狂抑郁中的沉浮与创作探索
2.1“迁杭”前郁达夫“愁”与“爱”的交织与呈现
郁达夫在创办创造社之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抑郁发作,随着创造社成立,他以十足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文学事业中,抑郁发作有所改善。1922年当他踏上给他带来无限悲戚故国的归途,他的心境也随之发生变化,感受到了迷惘与离愁。而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也在缓缓向前推进,社会洪流中一份子的郁达夫自觉地融入到革命中,与此同时,与王映霞的狂热的恋爱成为他人生命运悲剧的引线,促发着他躁狂的发作。直到1933年,郁达夫举家迁往杭州,他的心境逐渐呈现中人到中年的淡泊,归隐成为他迫切的愿望。精神世界的跌宕与起伏,交互出现,成为此阶段精神障碍的特点。
2.1.1《创造》发轫:职业困境中的“实现倾向”
1921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人在东京成立创造社,这就像是灰暗的前路出现了一道光芒,为郁达夫带来一线希望。但是在这之前,郁达夫曾经历了几场职业生涯上的失败,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这也成为此阶段“轻躁狂”发作的前提条件。首先是1919年9月得知外交官考试未能录取,为此,他在日记中写到,“庸人之碌碌者反登台省;品学兼优者被黜而亡!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①可见这次的失败,挫灭了他的报国之志。随后就是文官考试的落榜,屡次失败使得郁达夫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中,在给孙荃的信中就坦言了两次落榜的痛苦,他说“文少时曾负才名,自望亦颇不薄,今则一败涂地,见弃于国君,见弃于同胞矣,伤心哉,伤心哉!”②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单一的因素激发的,即“实现趋向”,这是一种可以保护和提升自我的意愿。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抑郁发作后,为了摆脱在情感、认知、意志行为上存在的障碍,郁达夫便想要通过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用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说”来解释,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类在漫长的自然演化中,已经获得了对自尊、友爱、创造性以及其他的潜能或品质的价值追求,这构成了“需要层次说”的高级需要的一部分,它可以“成为支配人的动机和行为的优势力量,促使人充分地实现其潜能。”③。
.............................
2.2抑郁的文本艺术呈现及躁狂的外化形式
抑郁与轻躁狂的交替出现给郁达夫的创作带来了不同的面貌。在抑郁状态下,他的小说在继承留日期间忧郁风格的基础上,开始关注“生的苦闷”和底层劳动人民。郁达夫已经将自身忧郁的人格气质转化为艺术气质,在痛苦中书写痛苦,郁达夫已经习惯处理自身的忧郁情绪,借助小说中的人物优劣的品质完成对自我的关照与反思,对纾解痛苦做出尝试。但郁达夫似乎对忧郁情绪处理得并不恰当,小说中喷井式的情感损害了作品的艺术风格。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的爱恋期间的写的日记更能体现出郁达夫轻躁狂属性,如果将郁达夫日记看作是一种文学体裁,在把握郁达夫日记独特的书写特点以及书写内容的基础上,阐释日记文学与郁达夫轻躁狂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2.2.1颓废美学的建构与不足
郁达夫回国后,告别了他“抒情的时代”,进入到纷杂的社会,在历经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失业的折磨后,生活的困境让他对身处的社会现实有了进一步认识。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郁达夫的视野开始变得开阔,在作品中展现的内容和题材更为丰富。从日本回国到奔赴广州这三年中,郁达夫共创作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其创作水平的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基本素材,书写自己失业与痛苦的,如《茑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等。另一类则是表现底层人民的劳动人民,表达对这类人的同情的,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这些作品与此阶段郁达夫忧郁的心境相符。这一节,将视野聚焦于郁达夫的抑郁状态,探究作品的题材、风格、人物的呈现与郁达夫抑郁及自我治疗的关系。
........................
第三章 精神障碍与创作的转向 ............................. 52
3.1 向“现实”转型的失败 ....................................... 52
3.1.1 顺应时代的革命热情 .................................... 52
3.1.2 “是文人,不是战士”:艺术自觉的形成 ..................... 57
结语 .................... 70
第三章精神障碍与创作的转向
3.1向“现实”转型的失败
在革命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时,有意投入到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快速适应并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革命中,是他们必须要经受的重大课题。郁达夫积极地向革命靠拢,来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但很快广州的革命现实就令郁达夫感到失望。在失望中“还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为革命发生,为获得革命成功提出自己的文艺观点。可是在“革命文学”的实践上却严重滞后于他的政治主张和文艺观点。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割裂,体现了郁达夫的创作必然受到独特个人气质的制约,而他的个人气质是在精神障碍的演进中不断被强化的,加重了个人气质的病态属性。所谓“文如其人”,作品风格无法从根本上脱离作家本人气质的制约,这也就意味着郁达夫实践下的“革命文学”呈现出了“阉割”状态,始终具有着浪漫主义的颓废色彩。某种意义上称得上是转型失败。
3.1.1顺应时代的革命热情
对待革命郁达夫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1926年3月,郁达夫因为自身经济原因应聘了广州大学文科教授,随同郭沫若、王独清等人从上海奔赴广州,与此同时广州如火如荼进行的国民革命同样吸引着这群青年。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所说,“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①郁达夫也说,“一九二五年是我衰颓到极点以后,焦躁苦闷,想把生活的行程改过的一年。这一年书也不读,文章也不写,从前年冬尽,到这年的秋后止,任意的喝酒,任意的游荡,结果于冬天得了重病,对人生又改了态度。”“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①从郁达夫本人上述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正处于抑郁状态,想要借助广州的革命气势给予他颓废的生活一些“激情”,虽说从表面上看,这种带有自我目的性地参与到革命中蒙蔽了郁达夫行为的纯洁性,但实际上,郁达夫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中就解释道了他的“苦闷”只能让他进行革命,他说道“青年的渴求光明,是自然性。求之不得,就不得不苦闷,苦闷之余,前面就只有一条去路。一条是走往消极方面去的自杀,一条是积极进行的革命、喋血。”②很明显,郁达夫并没有选择前者,而是在革命的路上奋身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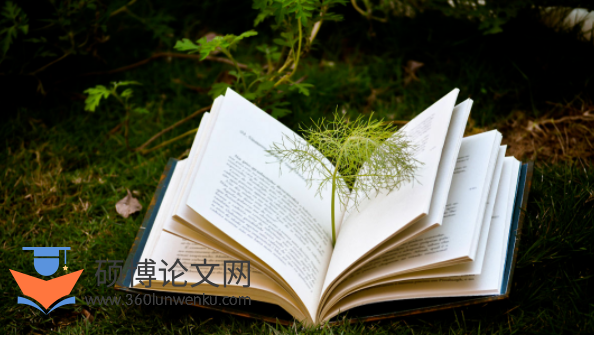
文学论文参考
...........................
结语
从郁达夫的精神障碍来谈他的创作,似乎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层透明的隔膜,就像“疯子”和“天才”之间也只有一线之隔一样。对于郁达夫而言,需要深入了解他的精神世界,沿着他的心路历程寻找他细腻情感的变迁历史,只有把握他独特人格生长与成熟的发展脉络和精神障碍的萌芽、发展与转归,才能理解他的文学创作。
本文将郁达夫的精神障碍纳入到文学研究中,通过郁达夫的日记、传记、书信等多方面的文献资料,梳理郁达夫的人物生平,尤其对他的精神世界做出整体性把握。郁达夫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发展课题的差异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的多元化同样导致了其精神障碍的原因的复杂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一生处在动荡漂泊的作家心中的悲欢与苦乐。从郁达夫的核心症状、心理症状群、躯体症状群等精神障碍的表现上,能够体会到一位敏感又多疑的作家是如何看待这个复杂世界的。郁达夫本人和他留下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躁郁症患者独特的视角,透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回到当时的时代场域和历史语境,体会郁达夫作为精神障碍的患者,他眼中世界的色彩变化以及为拯救心灵苦闷做出的努力尝试,并力图展现郁达夫创作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我们也可以窥见郁达夫在处理精神困境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上的态度,他将自身的情绪变化运用地游刃有余,他有意培养自己的忧郁气质以便他带来的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他又一直在“疗愈”精神障碍上做出尝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