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法律论文,笔者认为不论是刑事问题与民事问题的混同,还是刑事问题与行政问题的混同,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县知事及承审员在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模糊性,使得案件在处理结果上呈现出转重为轻的除罪化倾向。
第一章清末民初侵占罪的引入与发展
第一节侵占罪的引入及罪名的确定
一、取法日本:侵占罪的引入
(一)侵占罪在《刑律草案》中的初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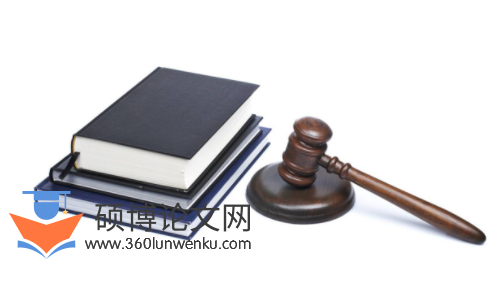
法律论文怎么写
关于侵占罪的规定,最早见于1907年《刑律草案》第三十四章“关于侵占之罪”。此章一开头便对侵占罪的内容和性质做了介绍:“此章所规定之侵占罪,若其成立系对于自己管有之他人所有物(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一项及第三百七十条)及准此之财物(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项),并已离他人管有之财物等者,则其罪之性质与盗罪及诈欺取财罪有异。”30即明确侵占罪的客体为自己管有之他人所有物,而这一客体的鲜明特征是其独立于盗窃和诈欺罪的关键,这种将侵占罪抽离于盗窃罪等其他财产犯罪的做法,明显与古代律例中有关侵占行为与盗罪、民事混合的规定显著不同。
从形式上看,侵占罪的立法体例与中国古代旧律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侵占罪独立于盗罪成为一章,那么侵占罪是否完全移植于外国的新罪,作为刑律起草者之一的冈田朝太郎有如下解释:“论者谓刑律草案所定罪名,皆系外国新名词,为中国旧刑律所未有,其实不然。即如本章之侵占罪,包括旧律之消费受寄物、监守自盗、冒认他人财物、转卖抵当物等种种罪名,并非新创名目。”31在清末礼法之争的背景下,他为了给新律中的罪名寻找旧律中的依据,将侵占罪之罪名等同于中国旧律中有关侵占行为的种种规定,这一观点虽然揭示了侵占罪在内容上与旧律藕断丝连的关系,却似乎故意忽略了侵占罪对传统罪刑体系的颠覆,因此对于侵占罪的罪名并非刑律草案新创名目这一说法,我们实在难以认同。那么侵占罪到底从何而来?其与外国刑法有何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仅仅考察侵占罪的法律文本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回到清末修律的历史过程中寻求答案。
............................
第二节侵占罪的设立及其修改
一、清末侵占罪的设立
1907年《刑律草案》引入侵占罪之后,为方便该罪的理解和适用,立法者在该罪各条之下标注法律沿革、理由和注意三项,以阐明各条之义。后来草案经修订完成并上奏皇帝,便交宪政编查馆考核,宪政编查馆分别咨询了在京各部堂官、在外各省督抚,这些官员相继对《刑律草案》中侵占罪的设立提出了签注意见,针对侵占罪设立与量刑是否适宜的问题,有如下质疑。
两广总督首先提出侵占罪罪刑不适当的问题,由于《刑律草案》第三百六十九条标明普通侵占罪基本沿革于旧律中的“盗卖田宅”和“费用受寄财物”条,两广总督便认为该条与旧律差异甚大:“费用受寄财产及强占官民山场55等项,定律各有专条。然因受寄而抎行费用之与恃强占踞者有别,故受寄费用,坐赃论罪减一等,强占则罪至满流也。今概名曰侵占,而罪名无轻重之分,似不若定律之明当。”56他认为此条没有依据侵占情节的轻重来定罪,认为侵占罪之规定过于笼统,没有反映出旧律中罪名的轻重有差,他的意见完全是以旧律为依据的,并没有理解新刑律中侵占作为新罪名已经将强占这一行为排除在外,而将其归为强盗罪之中。该意见提出后,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会同法部再次修订的《修正刑律草案》分别在第三十二章“关于窃盗及强盗之罪”的第三百七十一条及本章“关于侵占之罪”的第三百八十九条作出了回应,认为强占符合第三百七十一条“凡以暴行、胁迫得其余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或使他人得之者,以强盗论”,不必在侵占罪中另设专条。
............................
第二章龙泉司法档案所见侵占罪案件的特征与分类
第一节侵占罪案件的特征
一、起诉方式与内容的多样性
(一)公诉抑或私诉:起诉实践与立法的差异
提起诉讼是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并获得审理的第一步,现代刑事诉讼法严格规定了侦查、起诉、审判的诉讼程序,以及以公诉为主的起诉制度。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自诉”与“公诉”,基层刑事案件的启动多以民众向衙门提起诉状为准,官府对于诉状的手续做了诸多的要求和限制,此不赘述。
清末修律改变了上述情况,《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四十六条规定:“凡刑事案件因被害者之告诉、他人之告发、同法警察官之移送或自行发觉者,皆由检察官提起公诉,但必须亲告之事件(如胁迫诽毁奸通等罪)不在此限。”71从而确立了以刑事公诉为主,少数案件采取亲告即自诉的起诉制度,但此时侵占罪尚未纳入自诉案件范围。民国初年,地方和中央的司法仍然参照《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中的规定,直到1921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条例》才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诉”与“私诉”(即自诉)两个章节,其明确了包含奸非罪、和诱罪、妨害安全信用名誉及秘密罪、窃盗及强盗罪、诈欺取财罪、侵占罪、毁弃损坏罪等七项罪名的部分法条告诉乃论,72扩大了自诉的范围。其中侵占罪的私诉范围,仅涵盖三百九十一条(普通侵占罪)和三百九十三条(侵占遗失物罪),意味着第三百九十二条(公务或业务侵占罪)仍属公诉范围。由上可知,法律对侵占罪案件起诉方式的规定分为两个阶段,即1921年以前侵占罪采用完全的公诉制度,1921年至1927年期间,仅公务或业务上侵占罪采取公诉,其他两罪均采取自诉。尽管法律如此规定,然而由于北洋政府时期龙泉县长期实行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缺乏专门检察官的设置,1927年以前的龙泉司法档案中的侵占罪案件启动基本采用自诉方式。但是在少数案件中存在由县知事兼任的检察官提起公诉的公文,如民国十二年(1923)蒋建潘控任朝宗侵占公款案中县知事黄丽中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见下文。
..............................
第二节侵占罪案件的分类
一、以立法作为案件分类标准的局限性
《暂行新刑律》第三十四章有关侵占罪的立法将侵占罪分为三个具体罪名,分别为普通侵占罪(第三百九十一条)、公务或业务侵占罪(第三百九十二条)、侵占遗失物罪(第三百九十三条),其基本是按照占有权原的特征对侵占罪进行的分类。这一分类是基于立法的科学化、精细化的考量,与具体的司法实践所呈现的多样性与不规范性之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不能将其盲目地运用到案件的分类中来,因而对民国初期龙泉县侵占罪案件的分类仍需作更为全面地考量。
需要明确的是,侵占罪立法对罪名的分类仍然是我们划分案件的重要依据,其构成我们讨论案件分类的基础。依据侵占罪立法,普通侵占罪是指行为人侵占依契约或者法律管有的他人之物,业务或公务侵占罪是指行为人侵占依据特种公务或业务而管有的他人之物,侵占遗失物罪是指行为人侵占所拾得的他人遗失物。相较于普通侵占罪对占有权原的一般规定,业务或公务侵占罪、侵占遗失物罪是对占有权原的特殊规定。
以侵占罪的立法为标准,我们似乎可以将龙泉县的侵占罪案件分为普通侵占罪案件、公务或业务侵占罪案件以及侵占遗失物案件,但是通过案件的检索,我们并未发现与三百九十三条侵占遗失物相吻合的案件,此类案件在黄源盛编辑的《大理院刑事判例辑存》中数量也极少,仅存三个,而且基于此罪性质,其犯罪客体为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脱离本人管有之物,该物既已脱离主人管有,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很难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也将因案情十分轻微,难以进入诉讼程序。因此选编的龙泉司法档案中不存在侵占遗失物案件不足为奇。
..............................
第三章侵占罪案件审理中的刑事与民事、行政的混同.........................33
第一节普通侵占罪案件中刑事与民事责任认定、承担的混同..........................33
一、刑事抑或民事:侵占罪案件认定中的混同问题.......................................33
二、“偿赃即可免罪”:刑民责任承担上的混同......................37
第四章侵占罪案件中刑事与民事、行政混同的成因.............................49
第一节“民刑分立”背景下侵占罪法律的转变及其内在缺陷...............................49
一、由“民间细故”到“轻微刑事”:侵占罪案件的“变与不变”.........................49
二、侵占罪立法与社会情况相脱离..............................50
结论..................................63
第四章侵占罪案件中刑事与民事、行政混同的成因
第一节“民刑分立”背景下侵占罪法律的转变及其内在缺陷
一、由“民间细故”到“轻微刑事”:侵占罪案件的“变与不变”

法律论文参考
中国近代法律对于民、刑事案件的划分,最早见于1906年伍廷芳等奏《修律大臣奏呈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其将民事裁判定义为“关于钱债、房屋、地亩契约及索取赔偿者”,将刑事裁判定义为“叛逆、伪造货币官印、谋杀、抢劫、盗窃、诈欺、恐吓取财及他项应遵刑律定拟者”,126该折用列举的方式将刑事、民事案件区分开来。到了1907年,《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正式将刑事、民事案件的区别规定在法律中:“凡因诉讼而审定罪之有无者属刑事案件,凡因诉讼而审定理之曲直者属民事案件”。127按照法律规定,侵占罪立法被列入《暂行新刑律》之中,那么所有侵占罪案件无疑被归入刑事案件的范畴。
然而在“民刑分立”确立之前,侵占罪案件是如何定性的呢?有关案件的定性分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认为,在清末改革以前,统治者按照是否危害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将诉讼划分为“民间细故”和“命盗重情”。128清末以前的龙泉地方的案件审判便体现了这一点,如龙泉晚清时期的《收呈条例》载:“命盗重情,许即时禀报,其余一切田土口角细故,俱依告期递呈。”129因此围绕户婚、田土、钱债所产生的诉讼均被视为民间细故,而侵占罪立法源于盗卖田宅律、费用受寄财物律,其隶属于传统户律的范围,而侵占罪案件所涉及的标的也多为耕牛、钱银、田土、布疋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因此以侵占罪的立法渊源、案件的涉案标的观之,其与清末改革以前的民间细故并无太大区别。
...............................
结论
通过以上四章的论述,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首先,在清末立法中,侵占罪是如何确立的,其是否为完全从外国引入之新罪,其在民国立法中又得到了怎样的发展。我们知道在清末修律以前,中国传统旧律中并无近代意义上的侵占罪罪刑体系,只有几个与侵占行为相关的罪名分散在田宅、仓库、钱债各卷之中,分别为: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盗卖田宅、费用受寄财物以及得遗失物,这几个罪名被纳入“六赃”的范畴;在定罪和量刑方面,这些罪名皆没有与盗罪、民事规定区分开来。
侵占罪在1907年《刑律草案》中的初设,标志着侵占罪与盗窃罪等其他财产犯罪以及民事、行政规定的彻底分离,这一立法导向体现了西方近代刑法理论对传统旧律罪刑体系的改造,意味着侵占罪成为一项与旧律罪名几乎完全不同的“新名目”。这一新名目基本继受了日本《改正刑法》中“横領罪”的立法,按照构成要件的些微差别,立法者将侵占罪分别设立为:普通侵占罪、业务或公务侵占罪、侵占遗失物罪:与此同时,立法者在罪名的翻译上和立法的刑事政策上做了适应中国情况的改造:其借用中国旧律中的“侵占”一词来表达晦涩难懂的和制汉语——“横領罪”;并将日本关于“业务横領罪”的规定依据旧律中“官民有别”的理念扩充为“业务及公务侵占罪”;另外在刑事政策上,摒弃日本“横領罪”立法中刑事新派的“预防主义”主张,采取刑事旧派的“报复主义”主张。尽管立法者努力为新旧法律创造联系,但是经由外国刑法理论改造的“侵占罪”面貌焕然一新了。
参考文献(略)
